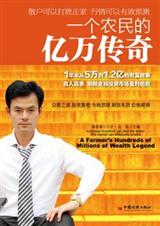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农民起义,起义者将朝鲜近代以来痛苦命运的根源归结为吏制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了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下,东学徒众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5月3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朝鲜南方重镇全州,兵指首都汉城,形势逼人。遭遇席卷而来的起义,朝鲜李氏王朝政府曾数次派兵镇压,甚至请求中国派出驻韩的北洋海军部分舰船帮助协同,出动了经中国武装和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前往戡乱,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而归。为尽快收拾近乎溃烂的局势,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朝鲜内政,在中国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
作者简介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自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陈志武教授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国内著名学术机构聘为访问教授。 陈志武教授一直是世界金融经济学和资本市场研究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 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学术奖励。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 ★*★.. ★*★.. ★*★.. ★*★.. ★*★.. ★*★..┗┛//.. . 【吃货自然萌】整理附:【】★*★.. ★*★.. ★*★.. ★*★.. ★*★.. ★*★.. ★*★.. ★*★..《草根家事》作者:我会做得好序言风风雨雨,刻画着人生的足迹;坎坎坷坷,勾勒着如烟的记忆。为了生活,别人说叫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欣赏欢乐与哭泣,更难有心思把愉悦与烦恼在文字中慢慢地梳理。待到离开岗位的刹那间,忽然觉得换了人间,原来是社会解放了自己,才有暇喘气、小憩。于是,或回首,或拾遗,才有了这篇《草根家事》,以此聊以自慰,藉以弥补对些许遗憾的唏嘘,虽然文字不那么尽如人意。...
东莞,被御马潜规则的那段日子 作者:王大少爷潜伏在办公室今晚,我是潜伏的,我像009一样潜进银声公司,偷窥着尊贵的御马,我不得不对这个汽车后市场的实力新星,来一次彻底的报复!据说,我一直倾慕的邻居大美女杨逸是这样变成剩女的,当她迈入25岁的年龄分水岭,正好就遇到多金、帅气的陈轩,陈轩是位无可挑剔的优秀男人,也是杨逸自第9次相亲以来,第一次看上的男人。为了成全杨逸的幸福,我自然就退了下来。俊男美女两人当场就擦出了爱火花,没两天就爱得难舍难分,杨家都开始张罗喜事了。那天,陈轩就驾着新买的皇冠过去接美女下班,本来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事。不料,杨逸回来后,就突然跟陈轩提分手了。后来,事情的真相实在是令人汗颜,这句原话是经过千辛万苦才从杨逸嘴里套出来的。...
少有人走的路2,与心灵对话第1节:前言前 言或许,你还记得《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的第一句话:人生苦难重重。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在《少有人走的路Ⅱ:与心灵对话》中,我要说的是:人生错综复杂。我还要提醒你,不要以为人生之路平坦无阻,只要你一步一步踏出去,就能不断前进。我个人心灵成长的进程,不一定是每个人成长会经过的道路。人生的路像一连串同心圆,从圆心向外不断扩张,其中的关联无法用任何简单直接的原理说明。可是我们不必坚持踽踽独行,可以向出现在生命中任何一股超过我们的力量求助。每个人对这种力量的观点不同,可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确实存在。此外,一路行进时,也不妨与他人结合,同舟共济。...
神秘特种部队真实故事:中国特种兵 作者:江清波杀破狼(1)四川大凉山古老的原始森林里,寒风猎猎作响,这里有全世界最美丽的索玛花,也有世界上最凶残的雪狼,此时这里正展开着一场最原始的猎杀。七名中国特种兵队员正在接受A军区最精锐特种兵大队“闪电剑”的考核选拔。就在一分钟前,大家都极度饥饿的时候,金锋为了给大家找一点食物,遇到了同样出来寻找食物的雪狼。现在四只雪狼就像围捕一头野牛一样撕咬着金锋,金锋的双手分别掐住了两条雪狼的脖子。他的眼睛因*而变得猩红,喉咙里嘶哑地发出野兽般的闷吼。求生的欲望让他忘记了疼痛,他的大腿已经被另外两头雪狼撕咬得血肉模糊,鲜血汩汩地往外流,在他前面十几米的地方丢着他的枪,还有几具雪狼的尸体。不远处几只雪狼正朝他的方向飞快地奔跑过来。...
《窄门》第一章我这里讲的一段经历,别人可能会写成一部书,而我倾尽全力去度过,耗掉了自己的特质,就只能极其简单地记下我的回忆。这些往事有时显得支离破碎,但我绝不想虚构点儿什么来补缀或通连:气力花在涂饰上,反而会妨害我讲述时所期望得到的最后的乐趣。丧父那年我还不满十二岁,母亲觉得在父亲生前行医的勒阿弗尔已无牵挂,便决定带我住到巴黎,好让我以更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一小套房间,弗洛拉·阿什布通小姐也搬来同住。这位小姐没有家人了,她当初是我母亲的小学教师,后来陪伴我母亲,不久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我就一直生活在这两个女人中间,她们的神情都同样温柔而忧伤,在我的眼中只能穿着丧服。且说有一天,想来该是我父亲去世很久了,我看见母亲的便帽上的饰带由黑色换成淡紫色,便惊讶地嚷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