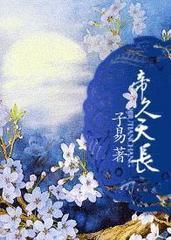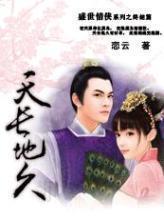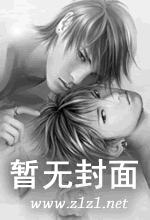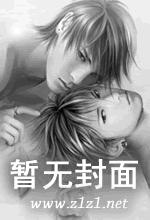天长久词-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打他出去便是!罗嗦什么?”
“打得了一时,打不脱一世,檀越,你往日一剑,差点要着他小命!他此番上山,定是寻你出气。”
阿沅听了,冷笑道:“岂有主人避不见客人的道理,他自来送死,我自成全他!”
和尚一见阿沅发作,连忙拦住,道:“檀越,这几日端午,小僧听闻山下的七柳镇有龙舟赛会。那里本是扬州城外一处市井,四面八方做买卖的,应有尽有。有这么一桩热闹在,檀越何必在寺中与一个晚辈致气?”
阿沅提着剑,转念一想,道:“也罢,我不与那晚辈计较。”
“是了,是了!正是此理!”和尚方才舒解,却瞥见菜园东边,五个土馒头,一旧,四新,还有墙下几处瓜架东倒西歪,几畦菜地脚印凌乱。
和尚心头一跳,问道:“小僧记得墙下那一个土馒头,埋的是檀越正月里打死的老虎,另外四个是?”
阿沅面不改色,也不答话,转出小门去了。
和尚惴惴不安。
他虽跟着阿沅下山,却禁不住回头。
他得空必得掘开那四座土坟瞧一瞧。
且说这时节,山气蓊郁,清溪幽涧,也有些山花烂漫。不知不觉,两人山径里走过一二十里地。
阿沅问道:“七柳镇的龙舟赛会,当真不凡?”
和尚道:“这是当然,年年都有精壮好汉,划长舟,破长浪,端的好看。”
“这条小路我倒不曾走过,距七柳镇还有多远?”阿沅问道。
“和尚左边是万竹岭,有条小道,不过听闻虎狼甚多,不取这条。和尚右边是赤枫岭,虽则远些,但路面清静,蛇虫较少,咱俩走这边。”和尚道。
阿沅道:“随和尚带路。”
那赤枫岭,因山上枫林秋日变色而得名,若赶上秋猎,丹枫下,呦呦鹿鸣,甚为可观。
这二人走到岭下,有座青砖路亭,傍着一口泉眼,供樵夫歇脚解渴。
阿沅与和尚正走得有些乏了,便进里头歇息片刻。
阿沅自亭间举目望向深山,这时节春尽,只有碧瘦的千崖万树。
和尚却看着壁上贴一张发白的旧告示,照念道:“此去半里为万竹岭,新有一些虎狼,伤害人命,现今杖限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切不可过岭,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
阿沅也看那告示,道:“此是三年前的告示,万竹岭上的虎狼竟还未寻获?”
和尚道:“非是那些猎户偷懒怕死,实则虎狼杀之不尽。和尚倒听闻有个义士,姓霍名珍,长住在万竹岭打猎。”
阿沅微微一笑,道:“有这么个好去处,不正是谢无忧用武之地?和尚该用三寸莲花舌、光明菩提心,劝他去。”
和尚且笑。
他二人谈论间,忽有一个妇人,匆匆躲进路亭。
只见这妇人年近四十,上穿浅青旧袄,下着旧裙,荆钗朴素,手里却抱着一个万字花纹锦缎包袱。不知包着什么东西,那般要紧?而那妇人面上,微微惊惶,但见着和尚与阿沅,却定下心,拣着阿沅身旁坐下。
阿沅将剑移在一边,并不说话。
和尚却向那妇人问道:“小僧法号飘瓦,不知女施主怎么称呼?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那妇人望望亭外,却不知她望向何处?听得和尚问话,才略一回神,低声道:“不瞒高僧,我家在此去三十里外的月塘镇,镇上人都唤我一声崔大娘。我有一个女儿,在七柳镇贺家庄上做针工多年。时值端午佳节,不得空回乡,我特去探她。”
和尚微微一笑,道:“月塘镇与七柳镇之间,有官道往来。崔大娘为何挑山间小道探亲?这小路实不好走,还有虎狼蛇虫出没。”
崔大娘却道:“我一介农妇,平素做些田间农活,一双大脚,山路也走惯。只是虎狼蛇虫,我独行也有些心怯。幸亏在这路亭遇见高僧,不知高僧宝刹何处?往何处去?”
和尚仍是微笑,道:“小僧在白马寺洒扫,可巧,也往七柳镇去。崔大娘若不嫌弃,不妨与小僧结伴同行,正有个照应。”
崔大娘面色一松,双手合十,连连谢道:“阿弥陀佛,多劳高僧。”
于是,歇息片刻,三人同行,先是走过赤枫岭,一路讲论许多。
崔大娘虽在乡野,也听说了扬州城里那桩桃花人头案。
她晓得曾有个白马寺的和尚出过力,不由开口多问一句,和尚笑而不答,她便留了心。
又行得几处山岭,下山渐渐望见一条长溪。
溪边屋舍连绵,官道人烟,马匹往来,岸边爆竹声声、咚咚鼓响,原是镇上百姓祭神。
三人走到山脚一个丁字路口,槐树头下挑出一个旗儿,是间茶棚。
和尚正欲与崔大娘作别,崔大娘却道:“有劳高僧一路照应,无以为报,不如借此处,请高僧一壶香茶、几笼素包子,心意虽浅,高僧莫要推辞。”
和尚摆手相却,不料崔大娘苦苦相求,阿沅心知有些古怪,道:“也是午时用饭,吃些素包子,也不错。”
说着阿沅迈进那茶棚,和尚只得跟随,崔大娘心上一松,紧随其后。
只见茶棚里,摆几张柏木桌,三面芦帘遮日。店里靠壁的磁盆架上,摆着贴着红纸的茶罐。瓦瓮灶上,蒸着高高笼屉的馒头。茶棚后边还有几个土灶,铁壶煮着冲茶热水。
阿沅拣着柜身对面一个干净桌儿坐下,小二已上前来问。
阿沅要了一壶龙井,六个素包子。店家应声,已转去后院提来铁壶。不一会儿,包子盛盘上来,三副茶碗也备。
和尚坐在阿沅下首,崔大娘打横而坐。
崔大娘暗暗将手里包袱放在桌子底下,忽而推说解手,便转去后园。店家此时已上来冲茶倒水,阿沅慢条斯理,心安自吃。和尚索性也不等崔大娘,吃素包子填肚。
半晌吃饱,那崔大娘却仍不回来。
和尚有些心疑,阿沅却已起身,提剑道:“走罢。”
二人付完茶水包子钱,正走出茶棚没几步,那店家却拿着个包袱,赶出门,叫道:“和尚落下东西!”
和尚回头一瞧,向那小二道:“那包袱是同行那位崔大娘的!等她回来,店家给她便是。”
店家不依,只奔上前来,将锦缎包袱塞到和尚怀里,道:“那位崔大娘早嘱咐了,说这包袱是和尚的要紧东西,不能丢失!”
和尚诧异,阿沅回头瞧那茶棚,亦不见崔大娘踪迹。
和尚只得打开那包袱,裹着的,不过一双绣花鞋罢了。那绣花鞋半新不旧,鞋底沾着干泥,五寸长短,与崔大娘的大脚相合。只是这也是一处疑惑,崔大娘自称有个叫碧珠的女儿,在贺家庄上做针工。既做针工,缝纳新鞋,想必不难,何须三十里路揣一双脏旧的绣花鞋探亲?饶是为了俭素,但这绣花鞋并不值钱,为何用上好的锦缎来包裹?
作者有话要说:
☆、高门悬尸
端午节,来七柳镇白水溪看赛龙舟的,人山人海,哪里去寻那个崔大娘?
和尚叹口气,只得将那锦缎包袱,搭在肩上,与阿沅往白水溪头看龙舟去。
路过一座城隍庙,却见一个五六十岁、粗衣打补丁的老僧官,正和庙门口卖跌打膏药的江湖郎中,坐一处遮棚长凳,吃花生,说兴亡。
那老僧官一见飘瓦经过,慌忙起来,迎上前抱住飘瓦,道:“宗师,怎么有雅兴下山游玩?《长阿含经》有几处要义,我甚是不明,夜夜看得心烦意乱,日日盼望宗师指教,没想到正遇着宗师经过,莫不是佛祖显灵?”
“圆智,你先松手,我有话问你。”飘瓦发声庄重,那老僧官立时肃然,道:“宗师,莫在日头下曝晒,到阴凉处说话。”
说着老僧官拽着飘瓦,到遮棚底下坐着,将桌上花生壳扫尽,涤净茶杯,倒一碗新茶,献给宗师。
飘瓦也不喝,只是让阿沅也坐。
圆智看一眼阿沅,问道:“这位姑娘是?”
飘瓦照例说是寺里种菜的,圆智艳羡道:“姑娘好造化,能在宗师座下种菜,日日聆听圣音说法,佛缘无量,佛缘无量。”
阿沅微微一笑,静坐而已,不搭这话。
飘瓦看阿沅一眼,道:“圆智,我这有个包袱,寄在你处,好生保管。”
圆智接过那包袱,道:“既是宗师所托,我自当收好。”
“还有一事,贺家庄在何处?庄主如何?”和尚问道。
圆智道:“沿白水溪,过东桥,柳林深处,高墙绵延半里的一处大庄院,就是贺家庄。庄主贺太公,为人宽和,家中两子,长子贺大,二子贺瓒。贺大在家守着田庄度日,贺瓒在扬州城做个刀笔吏,靠写些讼词谋生,也有三寸不烂之舌,起死回生之笔。扬州城里要打官司的,多去寻他写状纸。”
飘瓦心中有数,只问道:“写讼词据实以告,他家二儿子怎个起死回生之笔?”
圆智却收口,道:“此事说来话长,宗师若不急着回山,不妨在小庙多住几日。三千佛经,我有好些不通之处,还要宗师指点。”
飘瓦微微一笑,道:“也罢,晚些时候,再来问你这个滑头。”
阿沅瞧着飘瓦年纪轻轻,倚老卖老,冷哼一声。
和尚晓得惹阿沅发笑,起身要走。
不料此时,城隍庙门口,正经过一辆绑着竹篓竹筐的驴车。
车上一个老汉揽着柳鞭儿,膝头坐着个十岁左右娃娃。
那娃娃绑个冲天髻,身穿红衣小袄,抱着老汉腰身,正闭目垂涎好睡。——想必是赶集的爷孙俩。
那老汉赶车到城隍庙门口,卖布的卖糕的,各色小贩挨挤,哪有空地给他?
他只得转车头,另寻别处。
谁想正有放炮仗的顽童,三三两两,爆竹星子四处乱丢,惊得驴子性起!
那驴发起狂来,四处冲撞!踏碎果子摊,撞坏好些小贩……
驴车上的老汉惊得失措,紧紧抱着怀里小童,却不敢跳车。
情势正危急,飘瓦已赶上前去,挽住驴车的缰绳,脚下生根一般,咬牙立定!
那驴狂起来,岂是寻常揽得住?
和尚豁然一声,右脚踏出足有半寸深的脚印,牢牢牵住那犟驴!
众人看见和尚手段,个个惊呆。
才相持不久,那驴已老实了,于是,和尚缓缓将驴车往回拖拽,拴牢在庙门口旗竿石柱上。
那老汉抱着娃娃,由和尚搀下车来,纳头就要拜谢。
和尚扶住,圆智亦上来,请老汉坐在矮棚下,喝茶压惊。
那娃儿早已惊醒,偎在老汉脚边,十分怕生,圆智递果子给他吃,也不吃。圆智笑了笑,又与老汉打听几句闲话。
原来这老汉自马集镇来,来赶龙舟赛会,这四村八乡,人山人海,正好卖些竹器。
圆智看着他家孙儿,道:“这孙儿也长得机灵,怎不在家中陪着父母?”
老汉摆手道:“这娃儿是老朽在路上拣着的,老汉听他与家人走散,又说住在贺家庄。老汉顺路到七柳镇,搭他一程。却不知贺家庄在何处?也好送他回去。”
圆智道:“贺家庄贺大有个儿子,乳名叫阿拙,也是这般年纪,想必是了。”
圆智又看老汉不是本镇人,道:“老汉权把这娃娃寄在庙里,我差人送句话去贺家庄。他庄上若孙儿不见,自然有人来寻,也不耽误老汉的买卖。”
老汉听着也有理,便把那娃娃留下,他还有买卖要做,不敢多留,驾着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