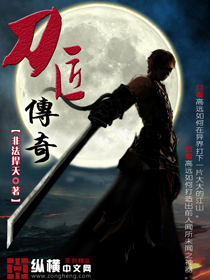菊与刀-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上种种说法详细而生动地说明了“恩情的力量”,要比其他任何总结性的结论更能说明问题。人们在接受恩惠时的心情往往充满了矛盾。在公认的社会关系中,人人都受到巨大的欠恩感的推动,竭力报答他人的恩情。然而,人们往往对欠恩感到难受,因而很容易产生反感。对于这种心态,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16【16萨评: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日本的小说家,翻译家,也是评论家,有日本第一才子之称,相貌似鲁迅,文风似沈从文,代表作为《我们是猫》、《伦敦塔》等。夏目曾经留学英国,是日本当时的英文名家,所以他的作品不但带有日本传统的风格,写法也易为英语世界所接受。可叹的是夏目的文风虽然潇洒,自己的一生却并不潇洒。他是家中幼子,因为是高龄产子,其母对他的出生感到更多的是“丢人”,如果不是他的姐姐怜悯,差点儿被扔掉。此后,夏目一生饱受神经衰弱、胃溃疡、痔疮等疾病的折磨,写小说就是他为了对付神经衰弱才开始的,却不料无心插柳。本书中提到的《哥儿》是他1906年的作品。夏目漱石姿容秀美闻名于世,现在日本一千日元钞票的图案就是他的头像。】在他的代表作《哥儿》中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哥儿是一位自幼在东京长大的青年,他起初在一个小镇上教书,但很快就对很多同事感到厌恶,无法相处。但和其中一位年轻的教师相处融洽。有一次外出途中,那位称做“豪猪”的新朋友请他喝了一杯冰水,价格是一钱五厘,大约是零点二美分。
不久以后,就有一位教师告诉哥儿,说他的好朋友在背后讲他的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位挑拨离间者的话,随后又想起了那个朋友请他喝冰水时的恩情:
虽然只是喝了一杯冰水,但是接受这种人的恩惠,实在影响到了我的荣誉。不论一钱还是五厘,接受这种人的恩惠,我实在是死不安宁……毫无表示地接受别人的恩惠,就表明我将他视为一个体面的人,尊重他。我自己没有坚持要为那杯冰水付账,而是接受了他的“恩惠”并表示了感谢,这种感激是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但我也有独立的人格。要我去接受别人的恩情,还不如让我偿还他一百万日元!
豪猪为我破费了一钱五厘,我觉得我对他的感谢至少值一百万日元。
第二天,他把那一钱五厘丢到了他那好朋友的桌子上。因为只有结束了对这一杯冰水的恩情,他才能真正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即豪猪侮辱性的语言。他们也许会互相殴打,但必须事先了结恩情,因为那已不是朋友之间的恩情。17【17萨评:这种思想,在西方显然找不到任何相似的线索,但如果到中国哲学中去找,就会发现其根源。中国古代的“士”对于接受恩惠有着同样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君子接受某人的恩惠,是看得起对方的表示——或者说是对方应该感到受宠若惊的事情。这种思想在西方看来简直不合逻辑,而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吃嗟来之食”的影子——当然,然后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了。】
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6)
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伤害,美国人认为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那些青少年帮派的不良记录或者患过精神病人的病历当中。18【18萨评:在美国人看来,得到对方的帮助,那么在适当的情况下给对方等量的回报——假如对方是在关键时刻帮助你的,则可以采取加权算法,就可以完成报恩的事情了,此后两不相欠。而东方的看法虽然物质上可以回报,但受过恩的人和施恩的人,是很难回复到“两不相欠”的相处状态的。】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人们觉得很少有日本人行事会如此极端。当然,那可能也是由于多数日本人比较懒散。日本的评论家在谈到《哥儿》这部小说时,说哥儿是“一个性情暴躁、纯似水晶、为正义战斗到底的人”。实际上,作者曾说,“哥儿”是自己的化身,评论家们也觉得如此。这是一个关于崇高美德的故事,受恩者只有把自己的感谢当作价值“百万日元”的东西,并相应地采取行动,才能彻底摆脱负恩者的境地。并且,只能从“体面的人”那里接受恩惠。哥儿在愤怒中,将自己得到的豪猪的恩情与长久以来一直关心自己的老奶妈的恩情进行了对比。这位老奶妈对他十分偏爱,总感觉家里人都不喜欢他,于是经常私下给他拿些糖果、彩色铅笔等小礼物,有一次还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始终如一的关怀给予了我巨大的快乐。当我从老奶妈手里接过那三块钱时,感到非常‘难为情’,但我把它当做借款。”然而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归还。那么,为什么至今仍不还呢?在与豪猪的恩情比较之后,哥儿自言自语地说那是因为“我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了”。这句话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不论感情多么错综复杂,只要“恩人”实际上是在自己或者说“我的”等级范围之内的人,或是他做了一些我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做的事情,比如在刮风的日子里帮别人拣起帽子等的人,或者是钦佩我的人,我们就可以对这种“恩情”心安理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恩情”就会成为人们难堪的痛苦。不论这种“恩情”是多么微不足道,人们也应该对此感到难过,这是一种美德。19【19萨评:如果刻薄地讨论日本人对于恩的看法,也许可以写出一部《丑陋的日本人》来。对于自己需要的东西,日本人认为从下位的人那里夺来,比从上位的人那里获得恩赐更有面子。因为上位的人是用来尊崇和进贡的,而下位的人天经地义就是来臣服和纳贡的。在日本人传统习俗里,人要么比自己高,需要百分之百的尊敬,要么比自己低,可以百分之百地欺压,就是很难找到平等的概念。】
日本人都知道,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过多的恩情都会带来麻烦。这一点可以从近期的杂志的“咨询专栏”中找到明显的例证,它有点像“失恋者信箱”,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的专栏。它的答疑毫无弗洛伊德20【20萨评:读到这里我曾经感到一愣,因为当时弗洛伊德刚刚逝世四年,想不到他的影响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都对这位犹太大夫的学说朗朗上口。要知道他的代表作《梦的解析》只印了600册,却卖了8年,我曾下意识认为他也是一个生前不太得志的大师。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将无意识行为与心理活动联系了起来,因为对人的潜意识研究有着深湛的造诣而闻名。他认为,人格缺陷或者精神疾患,往往与人被压抑的欲望或曾经遭受的伤害有关,其中,性欲在人类的欲望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对权力的追求都发源于原始性欲的不满。】精神分析的色彩,完全是日本式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在征求意见时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我的老伴十六年前去世了。我为了儿女考虑,因此我没有再婚,孩子们也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一种美德。现在,我的孩子都结婚成家了。八年前儿子结婚时,我退居到离家几个街区远的一幢房子里。有一件难堪的事情,三年来,我一直和一个夜度娘(被人卖到酒吧当妓女的人)在一起并发生了关系。21【21萨评:日语中称这种卖笑女子为“游女”,这种职业在今天的日本属于非法。日本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性服务,但法律禁止公开卖淫。】我听了她的身世后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了身,并把她带回家,教她礼仪,让她在我家做用人。她责任心很强,而且生活节俭。但是,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都因此而看不起我,把我当做外人。我并不责备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7)
那姑娘的父母似乎并不了解这一切。由于那姑娘已到了结婚年龄,所以她父母来信希望她能够早日回家。我同她的父母见过面,并说明了具体情况。她的父母虽很贫穷,但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同意她女儿留下来,就当她已经死了。那姑娘自己也愿意留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俩年龄的差异犹如父女一样。22【22萨评:这里体现了中国和日本的微妙区别。在中国,也不乏“老少配”的婚姻,但娶了年轻太太的老人绝对忌讳“如父女一样”这类说法,因为这隐含着讽刺二人的举止类似乱伦。而日本人则不怎么在乎。因为日本虽然大量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伦理方面却没有接受中国严格的观念。至今,“乱伦”依然是日本黄色影像制品的一大重要分类,而这里的中文报纸也报道过通过国际婚姻介绍嫁到日本来的中国新娘因为丈夫与其母有暧昧关系而震惊的新闻。抗战时期,中国方面曾经用日本伦理方面的松懈而指日本人是野蛮未开化民族。】因此,我也曾想过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都认为她对我的财产有所企图。
我长年生病,也只能活一两年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如果您能给我提出一些建议,我将不胜感激。最后我还要说明的一点,虽然那姑娘以前因为生活所迫而成为了“风尘女子”,但她品行端正,她的父母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
负责这个病人的医生认为,这个事例明显地说明了这位老人把子女欠的恩情看得太重了。他说:
你说的事情非常常见……
在正式解答之前,我必须说明,你似乎希望通过来信获得你所想要的答案,这使我有些反感。当然,对你长期的鳏居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却试图利用这一点来使子女们对你感恩,并使自己目前的行为正当化,我无法同意你这种想法。我并不是说你是个虚伪的人,但你却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如果你必须找一个女人,并且不想让你的子女们为你仍旧独身而对你感恩,那我建议你最好向子女们说清楚你必须和那个女人共同生活。当然,你过分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他们自然会反对你。不过,所有的人都有性欲。但是,人应该尝试战胜欲望。你的孩子们也希望你如此,因为他们仍旧希望你是一位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父亲。然而,你让他们失望了。我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他们是自私的,但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你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子女们结了婚,在性欲上得到了满足,却拒绝自己的父亲有这种要求。23【23萨评:在日本社会,如果作为一个正经话题来谈,性欲问题是可以公开谈论的。相对来说,日本社会对“性”的话题并不排斥,也不愿意为其设定各种限制。但是在中国,如果给人这样写信,对方大约只能火冒三丈。】但你的孩子们却有不同的想法(像我前面所说的),你们这两种想法发生了冲突。
你说那姑娘和姑娘的父母都很善良,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