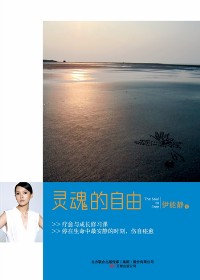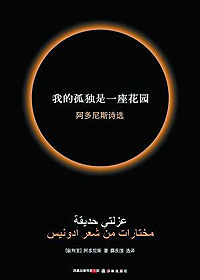序 发乎情,不止乎礼止 庵 家辉兄的文章,我最早是在《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读到,还记得专栏的名字叫“深港情书”。从前废名说梁遇春,“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镜子一样,把什么都收藏起来。”(《〈泪与笑〉序》)我对家辉兄亦有此等感慨,我佩服他文思敏捷,而且无所不谈。 我们写文章,常常是“发乎情,止乎理”;家辉兄则是“发乎情,不止乎理”。他好像有意要把《明暗》这类文字,与他那些看来分量更重的评论作品区分开来。周作人在《美文》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所云“论文”,即essay,通译随笔。他接下来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应该是专就抒情一路而言。后来周作人...
序(1)李菁是2001年到的生活周刊,2001年我们刚被赶出净土胡同,在安贞大厦找到了一个安逸的家,她就来了。刚来时候,我对她没有印象,依稀中似乎听李鸿谷介绍,她是刚来的记者。那时候李鸿谷也是刚从武汉到周刊不久,立足未稳。社会部有一个与高昱几乎同一年入职的老兵王珲,李鸿谷难以调教。随后几位都是在李鸿谷之后入职,如巫昂,本名陈宇红,福建人,这个笔名可充分展示她身上那种不会枯竭的欲望。如郦毅,个子高高,说话似乎总胆怯着细声细气,她是高昱的同学。如金焱,一个喜欢穿靴子的哈尔滨姑娘。2000年我说服李鸿谷到北京,就是希望他能拉出一支可在周刊开始采访突破的队伍,改变周刊原来不以事实轻易地说三道四的习惯。为了充分调度他的可能性,我把原来做社会报道已经形成定势的高昱专门调去搭起一个经济部,把地盘腾给李鸿谷。与社会部相对,经济部当时几乎全是男丁:高昱加上陆新之,加上李伟与黄河。...
什么是诗歌精神?(1)——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 什么是诗歌精神?当我想到这个句子,自己都哑然失笑。在号称后现代的今天,谁敢这样提问呢?对于习惯肢解诗歌器官的学者,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对于热衷以小圈子划分地盘的诗人团伙,这个问题太宽泛了。简单地说,它太“大”了,大得容不下流行的诗歌分类学。这个问题,不是要在一首诗里翻读出一段时间、一种观念、一个流派。恰恰相反,它之提出,正在于真正的诗人对任何分类法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或许,发明“诗”——“寺中之言”——这个汉字的人,也已一举造就了我们的命运:像一名巫师,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又在关联中醒悟真谛。我们知道,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每当我们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聚焦于一个句子,就通过写,在贴近它、确认它。我们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这是为什么,我写得越多、越久,离所谓“当代”越遥远,却感到屈原、杜甫日益...
1在某一天夜里,我与老罗一起被炒了鱿鱼,酒后我自己坐路边,手里握着一把跟随我很长时间的匕首,想着要如何结束我的生命。当然,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与继续生活下去同样需要勇气,然而,我一次一次的选择了逃避。我坐路旁,望着无尽的柏油路以及巨大空荡的建筑物,发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也断此生——希望这样能够摆脱这个世界。 的确我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汽车,没有相貌,也没有才华,但这不能决定我的人生,人都是有理想有前进的目标,当你失去了希望,生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所想的,是他妈的我这半辈子的衰,遇上那些狗屁倒灶的事,也不知道我还能再承受多少。 许多人说他们真希望死掉算了,但是他们中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自己真会寻死?又有多少人真的会采取行动把自己干掉?大半的时间,人们只是寻求同情或怜悯罢了。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打打身上的尘土,走回家里。...
[综漫]绫女 作者:水涸湘 不真实的世界 在充满奢靡味道的大床上,体态修长的银发男子从身下,显然已经在欢爱过程中陷入昏迷的男孩的身体撤出,似乎也用些劳累了,但刚刚的欢爱显然是让他极满意的,此刻金色的眼睛半眯着,打量着床上的男孩,眼睛里流光溢彩,煞是引人。 床上的男孩子有一头柔软的银紫色短发,只有十二岁左右,柔软的身体,细腻的肌肤以及极力隐忍的呻吟都让男子回味不已。然而毕竟是年幼,即使已经是很优秀的孩子了,也还无法适应这种属于成年人的美丽运动。太娇弱也太易碎了,让人不能毫无顾忌的享受呢。男子微微叹了口气,心情有些下降,不过马上又愉悦起来,这么好的素质,再过上几年就能变得非常完美呢,那么要不要将他带在身边养大一些呢,可是养宠物很麻烦的啊,苦恼啊。...
序(1)身材瘦弱,气质优雅,白皙的瓜子脸,一双明亮深沉的大眼睛,挺立笔直的鼻梁,少有的微笑中稍显抑悒,给人以自尊心极强之感,似乎是《红楼梦》中林姑娘淒美形象的现代版。 这是1980年秋季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杨劲桦的瞬间印象。 我看过彭明先生写来的推介信,问她为什么要研究瞿秋白?那时,瞿秋白研究还是禁忌的敏感课题,明智之士谈瞿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位小姑娘却迎难而上,令我有些好奇。我问她的问题,她不正面回答,我也就不再问下去了。过几天,她按约定来看资料,依然是一身蓝布衣裤、白布衬衫,一双旧皮鞋,虽素朴而不掩优雅。我把大堆瞿秋白资料交给她,她轻轻地说:“谢谢,老师。”就坐在门边一张临时安置的书桌前默默看起来。那些资料,是我准备写《瞿秋白传》多方收集的,她写一篇文章是足够用的。当时,我正在修改《伟大的开端》书稿,没有太多时间跟她聊天和讨论。...
那天使的生日关你屁事!天使是战狼的朋友呀。战狼又是谁呀?战狼就是居方。战狼和居方是一个人。战狼是我的好朋友。 关于写作的目的。我感动于战狼对天使的柏拉图式的爱恋,因此在次为这段爱恋著书立说,阐释这种理论。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战狼还是作者本人,都还没完全超脱叔本华兄所谓的“生命意志”的理论,但作者尽力创造一种新的体系,使人尽量超脱世俗的羁绊,在爱情中自由、清纯而高远。 还要说明一个问题,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吸取了丰厚的营养和支撑。他们是:米兰.昆德拉大哥,弗兰茨.卡夫卡大哥,叔本华大哥,尼采大哥,弗洛伊德大哥,屠格涅夫大叔,歌德大叔。还要感谢北大文系毕业的###同志,他的《香草山》像一碗“毒药”,直接导致了我大学时代爱情理想的萌生和发展。还要感谢王小波和李银河,尤其是王小波,他的《绿毛水怪》以及《黄金时代》至今让我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