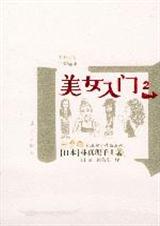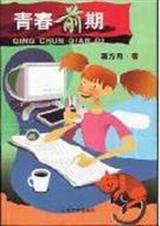:**钱学森传王寿云 等钱学森(一)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名家治,后以号行)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3岁时随父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
我们的目标是从这条小河的源头出发,抵达小河与另一条河流的交汇处,全过程考察小河的流向,绘制小河流程图。 前面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坡阻断了小河前进的步伐,机智的小河调转头来,温柔地依附着小山坡,不动声色地拐了个弯后,完成了转身的动作,缓缓回流了过去。向东继续前行了十多公里后,小河终于找到了出口,缓缓地流淌着,汇入了另一条河流。 站在河流的交汇处,同行的老孙感叹着说:“河流是我们的老师啊!当人生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也许转身就是方向”我对老孙的话深有同感:家乡野蚕的行踪也具有类似河流转向的特征,当它们自下而上吃光了一个枝条上的树叶后,总会转过身去,将后方变成前方,将来路视为出路,重新出发,去寻找下一个蚕食与生存的空间,不断占据新的枝条。...
那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大约八点半,医院来了一位老人,看上去八十多岁,是来给拇指拆线的。他急切地对我说,9点钟他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希望我能照顾一下。 我先请老人坐下,看了看他的病历。心想,如果按照病历,老人应去找另一位大夫拆线,但那至少得等一个小时。出于对老人的尊重,正好当时我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就来为老人拆线。我拆开纱布,检查了一下老人的伤势,看到伤势基本已经愈合,便小心翼翼地为老人拆了线,并为他敷上一些防止感染的药。在治疗过程中,我和老人攀谈了几句。我问他是否已经和该为他拆线的大夫约定了时间。老人说没有,他知道那位大夫9点半以后才上班。我好奇地问:"那你还来这么早干什么呢?"老人不好意思地笑道:"我要在9点钟到康复室和我的妻子共进早餐。"...
云天情缘 情缘 第一章 项链 春秋来了,大地渐渐地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 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明山县政府纠正冤假错案最多的第三年。 云天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在信仿办工作。上班没几个月,所接触的来访者,几乎都是为自己鸣冤叫屈要求落实政策的,唯有一个跟自己一般年纪的姑娘,才是为父亲伸冤的,她每隔三五天就来一趟询问,来的次数多了,自然便熟悉了。云天见那姑娘满面愁绪,像含着满嘴的黄连似的,心里便生出几分同情。 有一天,姑娘不知是因为我领导没有结果,还是其它原因,竟无助地躲在门边用手捂着脸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云天见此便有些于心不忍地走过去劝慰她说:“不要哭了要想开些,只要你父亲没有犯罪,迟早有平反的一天。” “是吗?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哟?”姑娘见云天来劝慰自己,便有些难为情地用她那一双盈满泪...
【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有个特像相声演员大助花子的人,也叫上她吧,调节调节气氛。” 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中濑。她确实像极了大助花子,但也很像快餐店“不二家”门前站立的卡通人偶。总之能喝、能说。经常一个人在那里装疯卖傻,活像一个小品演员,逗得大家大笑不止。大醉之下,甚至会与男同事勾肩搭背。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本人头脑极其聪明,且充满女性魅力的话是无法做到的。无须赘言,中濑非常可爱,极有人气。但不可置疑的是她也是一个大活宝。尽管如此,她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却是最受男人喜欢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士不少,可是否真的如此就不好说了。就是真的受欢迎,也有层次差别。有的女士仅在举办宴会时会被人想起,有的却时时被挂在嘴边。中濑属于后者。...
这是一个爱心激荡的故事。年轻的妈妈吉娜用自己的真情真心联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妈妈,做了一道牢固的“妈妈墙”——“世界年轻妈妈联盟”。她们无私地帮助危难和疾苦 的妈妈。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同一个人,她就是世界魔法妈妈——J·K罗琳。 绝症女孩用生命祈盼第4部书 1999年夏天,家住纽约州北部的8岁小女孩凯蒂·霍克,最大的愿望是连续跳绳能突破100下,正当她全力朝这个目标冲刺的时候,她长期背痛的原因查清楚了:她的肾上长了肿瘤。 凯蒂的父母一下子被巨大的灾难击得晕头转向,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凯蒂的病情根本无法控制,癌细胞迅速扩散,短短的时间内,凯蒂作了七次化疗,肺部做了三次手术,肝部做了一次手术。...
老布什卸任总统后不愿随俗写自传出书,但那本写作近六十年的书信集却显露出一个平实却又不平凡的人生故事。而他的文采以及细腻的感情更是跃然于字里行间,例如他在1958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就把一个年轻父亲对早逝女儿的伤怀写得丝丝入扣。 “我总把萝宾当做我们这个家庭中活生生的一份子,芭芭拉和我也不知道这感觉会持续多久,但我们希望到了八十岁都还保有这种和她在一起的亲近感。那该多奇妙啊!在那个年纪却仍拥有一个美丽的三岁女儿......她不会长大的。” “我们这个家缺少了一个什么?在四个男孩活蹦乱跳的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个金发女孩来平衡一下那四个平头;在那些玩具碉堡和无数的棒球卡片中,我们需要有个娃娃屋;在我发脾气时,我们需要一个女孩的哭声而不是男孩的申辩;在圣诞节时,我们更需要一个小天使......我们需要一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