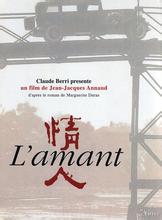最后的荣耀-第8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行!不行!”那位阿姨大惊失色,一把扯开了我们牵着的两只手,命令我立刻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小雪在一旁天真的问:“阿姨,为什么不行?”
那位阿姨蹲了下来,握住她的小手,和蔼地说:“傻孩子!女孩子怎么能和男孩子睡一块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睡一块,但我知道我一定是闯了祸。因为从那以后,我在玩耍的时候,总有阿姨特别留意我。还有一次,我听见阿姨小声地对我妈妈说:“你的儿子有点早熟。”我不明白“早熟”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决不是在表扬我。她们就这样观察了我几个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这才放下心来。
那时,我以为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区别就是头发。女孩的花衣服没什么稀罕,我也穿过。那是有一次阿姨教我们扮家家玩,不知是什么念头促使那位阿姨突发奇想,让我扮演妈妈,让小雪扮演爸爸。于是我就穿上了花衣服,所有的孩子都笑翻了。他们不是笑我的这身打扮,而是笑我的头发。其实我那时白白净净,打扮起来决不会输给女孩子,唯一糟糕的是头发太短。阿姨好不容易用两根皮筋在我头上扎起了两撮头发,权当小辫。我没有去照镜子,但我知道那一定很滑稽,因为连小雪也笑得坐到了地上,抱着肚子直叫疼。
然后是表演。我一手抱着布娃娃,一手装作在做饭,口里还念念有词:“宝宝乖,宝宝乖,妈妈喂你吃饭饭。不许哭,不许闹,还不准尿尿。”这一回笑倒的是阿姨。
轮到小雪上场了,她在嘴唇上贴了两张黑纸片,当作胡子,两根小辫一翘一翘的,根本就不像“爸爸”,我看了也想笑。
她从我手里抱过布娃娃,很认真地说:“宝宝乖,爸爸下班了,现在教你做游戏。”
“他不会做游戏,他要吃饭饭!”我从小雪的手中抢过布娃娃,认真地说。
“他会做游戏!”小雪伸手来抢,抓住了布娃娃的两条腿,我紧紧抱住布娃娃的脑袋不放。
我们就这样将布娃娃拖来拔去,谁也不让谁。
“不会!”我叫道。
“会!”她也叫道。
“不会!”
“会!”
“他还没有长大!”我解释道。
“你为什么不让他长大?”小雪似乎很不满。
“这布娃娃又不是我的。”我傻乎乎地回答道。
然后我们的耳朵里立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笑声……
只有一次,我把小雪弄哭了。罪魁祸首也是头发。
上面说过了,我以为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区别就是头发。我不明白为什么男孩子只能是短头发,只有女孩子才能留长发、扎小辫。于是我就去问阿姨。阿姨说:“男孩子留长发就不像男孩子了。”我又追问:“为什么男孩子留长发就不像男孩子了?”阿姨说:“这孩子!阿姨跟你说不像就是不像!”
看来,连阿姨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就去问小雪。
小雪说:“男孩子留短发才像男子汉,女孩子有辫子才漂亮。”
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正像是男子汉,而她也确实很漂亮。
小雪很爱护她的辫子,有时阿姨也会帮她梳小辫,我就在旁边看,看着看着也就学会了。有时我很热心地想帮她梳小辫,但她总是不愿意。终于有一次,我趁她不注意,解下了她一边的小辫,然后向她示意我能够像原样帮她梳好。哪知她一摸小辫散了,立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立刻号啕大哭起来。
阿姨们闻声赶了过来,将我痛骂了一顿,罚我去面壁。
面壁我倒不怕,让我伤心的是小雪有好一段时间不理我。
好在小孩子都不怎么记仇,我们很快又和好如初了。
和小雪在一起就是这样使人快乐,快乐得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很快我们都到了入学的年龄。
入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那是一个孩子长大的第一个标志。但我却有些快乐不起来。因为附近有两所小学供我们选择,谁知道小雪的妈妈给她选的是哪一所呢?
离开幼儿园的前几天,小雪告诉了我她要去的学校,正是我要去的那所学校!
我高兴极了!
开学典礼的那一天,我又惊喜地发现小雪和我分在一个班。
崭新的一天开始了。
幸福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
2001年1月6日初稿
2003年8月9日修订
第四章 梦碎
我的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我的父亲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他们的生活是严谨的。
我还有一个弟弟,他小我三岁,名字叫吴勤义。
我们的家庭有勤劳的传统。父亲是做菜的好手,所以每天买菜做饭的事就由他承担,我刚上小学那阵子,他还要天天接送我。母亲呢,每天一有空就整理整理这里,打扫打扫那里,晚上要哄弟弟睡下了,才开始备课和批改作业。所以每天第一个起床的是父亲,最后一个睡觉的是母亲。我总觉得他们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每天都要拖一次地板?母亲说:“这样家才像一个家。”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两天或者三天拖一次地板,难道少拖两次地板家就不像家了吗?我不敢继续追问,我怕挨骂。
为了培养我和弟弟从小爱劳动的习惯,我们年满三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糖果的奖励,我们干起活来特别卖力。等到糖果对我们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干起活来就推三阻四,纯粹是为了不挨骂,才老老实实把活干完。这些都是后话了。
上小学的那一阵,我倒确实是勤劳过一段时间。人一旦勤劳惯了,突然让他什么也不干,说不定还会生病。我那个班上,有几个同学喜欢乱扔东西,他们的桌椅周围经常有纸屑、铅笔屑,我看惯了家里干净的地板,见到这样的情景很不舒服。终于有一次忍不住,将本来由值日生负责的事做了。事情巧得有些离谱,班主任袁老师刚好在这时走了进来。结果可想而知,袁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让我沾沾自喜了好久。
小雪也替我高兴,看到她高兴,我也就更高兴了。只要能让小雪高兴,就是老师让我值日一个月我都愿意。
我和小雪嘛,还像幼儿园时那样,一下课,我们就手牵着手一起玩儿。那时候的小孩子都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一旦进了小学,就不再随随便便牵手,而是女孩子一堆,男孩子一堆,各玩各的。只有我和小雪是唯一的例外。刚开始大家还不怎么在意,可是看我们从一年级一直牵手到二年级,就有人要说怪话了。
有一个小胖子—;—;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有一回跟在我们后面笑我们。他一边用食指在脸上比划,一边大声说:“羞啊羞,小雪要嫁给勤勇作新娘子喽!”
小雪恼了,转身就是一脚,骂道:“多嘴婆!”
谁也没想到,就这么轻轻一脚,小胖子就栽倒在地,居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眼睛哭成了一条缝,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不停地擦着眼泪,那模样实在滑稽。
周围的同学们都围过来看热闹。有几个好事的还在那里起哄:“喔!被女孩子欺负喽!”“喔!连女孩子都打不过喽!”
我往前站了一步,预备等小胖子站起来反击的时候保护小雪。
哪知小胖子太不争气,只是一个劲地哭,好不容易说出一句话却是:“呜……你打人……呜……我要告老师……呜……”这才慢慢站起来,连裤子上的尘土也不拍,呜咽着走了。
“你快去告吧!”我没有忘记讽刺他一句。
我打心眼里赞赏小雪的举动,她可不像有些女孩子,碰到这种事只会哭鼻子,白白被人欺负。
然而小胖子的话也让我很受用,小雪将来会成为我的新娘,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从小胖子嘴里说出来,说明大家也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瞧,多般配!
我于是常常幻想小雪戴着红盖头,坐着花轿的情景。那抬轿的轿夫还是陈志超呢!
—;—;请原谅我的幼稚,那时候的我还真没见过一场真正的婚礼,所有关于婚礼的知识全来自幼儿园老师讲的“抬花轿”、“拜天地”。
但是事情往往不按你想象的来,要是那样的话,世界上也就没有“痛苦”这个词了。
三年级开学的那一天,我发现小雪不见了。
我快要急疯了。
直到班主任在课堂宣布:因为小雪的爸爸调动工作,所以她也跟着转学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个暑假。
我那天直想哭鼻子,但在同学们面前我不敢哭,强忍着回到家里,就立刻钻进被窝蒙上头。
除了哭,我还能做什么呢?小雪走了,没有跟我告别,也没有留下一件能让我想念她的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她不让他的父亲别调动?
为什么她不能等开学了以后再调动?那样我们也可以见上一面啊。
为什么小雪不来向我道别?我们不是形影不离的一对吗?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现在我想明白了。一个孩子怎么有能力左右她的父母呢?小雪一定也急着把这件事告诉我,可是她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又怎么告诉我呢?打电话吗?那时候电话可是个奢侈品,只有校长和厂长的案头才摆放着珍贵的电话。写信吗?那种离别的千言万语叫一个才二年级没学过写信的孩子如何表述呢?
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一眨眼就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蜻蜓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舞,大雨一来,就立刻无影无踪。谁又能预料到什么时候下雨呢?
小雪一定是和我一样痛苦吧?她能够承受这种痛苦吗?我虽然是一个男子汉,但是我承受不了。
知道小雪转学的第二天,我就伤心地告诉妈妈:“妈妈,小雪转学走了。”
妈妈说:“哦。”
我又去告诉爸爸:“爸爸,小雪转学走了。”
爸爸问:“小雪是谁?”
我明白了,大人的世界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的世界大人也不会理解。
我只有用被子蒙着头,自己伤心了。
这么一来二去,我开始喜欢睡那种别人称之为“懒觉”的觉了。这种觉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世的伤心、生命的苦难、心灵的眼泪我体验了,我品尝了。这就足够了。
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雪了!
她走了,但不是什么东西都没留下。她给我留下了一个很美的,但是破碎的梦。这个梦永远珍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是我心灵的天堂。它能在我饱受挫折后给我抚慰,它能在我不被人理解时给我力量。
小雪走后,我的脾气变坏了。在学校里我经常和人打架,回到家里,如果弟弟来烦我,我就给他一个耳光让他哭,为此我没有少挨揍。
终于班主任袁老师利用星期天来家访了。不巧得很,爸爸妈妈带弟弟去看病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尤其不巧的,是我正在干坏事。
前两天老师刚讲了王羲之练字的故事,我听了很不服气。我想,像王羲之这么练字,又费时,又费力,如果我肯练字,一定比他好多了。
正好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那就任由我大闹天宫了。王羲之的字太小气,用的毛笔也是细细小小,我得找一把什么笔来胜过他。
我的目光凝固在了妈妈放在墙角的那根比我还高一米的拖把上,就是它了!
用墨汁是不行的,那会留下作案的痕迹,还是用清水吧,反正我又不写给别人看。
于是我提了小半桶清水放在客厅里,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十年以后,当我看见有书法家提着一根沾满墨汁的拖把,在一张大白布上跑来跑去的时候,就不由得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