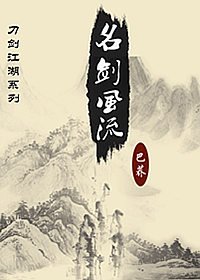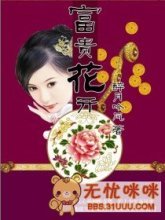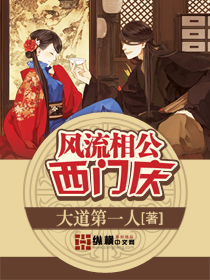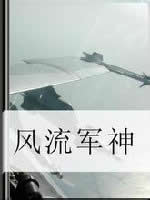富贵风流-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影响来说,她让襄王去求陛下处置柳大人,也是易如反掌。即使陛下明辨是非,恐怕也难免心中要对柳大人多几分不满,觉得柳大人伤了他们手足之情。那个时候,柳大人的仕途只怕是再无上升之望了。”
为商人者唯恐钱财损失,为官者则唯恐仕途难更上一层楼。白南山不是第一天和官吏打交道,自然不会不明白对于官员而言,仕途精进远比积累财富重要。
此时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随从说了句请大人下车,然后便为柳梧打起了车帘。柳梧沉默着起身,但当他扶着随从的手就要下车的那一刻,他突然转过头来对白南山说道:“白老爷说的事儿本官可以同意。不过本官希望白老爷明白一件事儿。锦上添花的本事本官有,但雪中送炭的能耐,没有。”
白南山微微一笑,拱拱手,什么也没说。
作者有话要说: [1]请别问东主为什么这里突然串戏到西游记……东主布吉岛
☆、宫闱内
此时皇宫中,有一个人的烦恼也许不比柳梧刚才的少——那就是皇后。
皇后看看坐在自己下首一直擦眼泪的魏余欢,又看看坐在对面转着手里的佛珠不说话的太后,突然觉得自己在这儿就是多余……对于皇帝关襄王的原因,皇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原因很简单,朝堂倾轧,皇室手足秘闻,这类东西即使是这宫里最尊贵的女人,最好也是能装看不见就装看不见——这也是太后这么多年来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教会皇后的。
连皇帝的亲妈都不能多说什么的事儿,她这个做妻子的最好也别插嘴。
然而皇后作为一个旁观者能这么洒脱,魏余欢这个当局者就不可能了。她是襄王府实际的女主人,是穆鸿烈的侧妃,就算她对穆鸿烈毫无感情,她都不可能不来求太后饶恕鸿烈,不可能不问一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何况,人非草木,相伴近十年,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
魏余欢用带着些哀求的眼神看了看皇后,皇后本来想装作看不见,但想了一下终究还是有些于心不忍,“母后,襄王这档子事儿……您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说饶恕他?但如果这事儿压根儿跟太后没关系呢?说给魏余欢一个明白?那不就等于说这事儿有内情么?反正怎么说都不对。皇后心里叹了口气,干脆就住口了。
太后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儿媳妇儿,心道年轻人到底心软守不住。但考虑到皇后的身份,她就还是给了皇后一个面子,接口道:“鸿烈失礼,你们都不要给他求情。他买了温家的宅子,不知禀报也就罢了,居然还和那个温庄和纠缠不清,还敢到我面前来说些没分寸的话,让他闭门读书我都觉得轻了!”
既然魏余欢非得问个明白,那太后也就干脆给她一个‘明白’。其实太后自问自己这也是在帮魏余欢了。鸿烈的确是因为温宅而出事,也的确是因为和温庄和纠缠不清而出事。不过即使是太后,这个话也就仅仅能到这儿。再往下说,那就要说到皇帝不希望别人知道的部分了。
魏余欢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鸿烈买温家宅子的事儿曝光,被皇帝和太后责骂,而皇帝和太后很有可能言语中攻击了温庄和,结果鸿烈就犯起了牛脾气,顶撞了这二人。甚至可能还说了一些类似于他要娶也只娶温庄和这样的话。所以,才招致这样的祸端。而这样的理由偏偏是不能让天下臣民知道的——毕竟,堂堂吴国亲王为了个女人顶撞君王和母亲,的确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儿——因此就只好隐去了原因,只说鸿烈顶撞太后。
不孝虽然不是什么美名,但总比因女|色而不孝要好听一点儿。
这么一想,倒是也能说得通的。
不过皇后却觉得这事儿古怪的很。如果太后所说的就是实情,那就等于皇室几乎没有采用什么遮丑的手段就直接将罪名公之于众了。
这很不符合常理。因为在皇后的记忆中,在她嫁入皇宫的这二十年里,就从没听说过有哪件可以称之为丑闻的事儿,没在披露时被尽量减轻其丑闻等级的。
顶撞母亲是为不孝,这样的事儿即使是在寻常人家都是要极力掩饰的,何况皇家呢?
如果这个罪名都被拉出来用了,那就说明鸿烈犯的错儿,恐怕远远超过不孝,或者不孝的程度远远大于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在这两种可能里,皇后倾向于第一种。这种推测的依据很简单,其实看看太后说起这事儿时的表情就应该知道了——作为一个被小儿子忤逆了的母亲,太后显得太平静了。
而这种平静不可能是随着时间过去,而慢慢冷静下来的结果。
因为皇后很清楚一个母亲的心。一个母亲即使是听说别人家出了忤逆子,都不免会设身处地的为同是父母的人不平,为他们感到愤怒,更何况现在是太后自己经历了这样的事儿?
也许皇后那个‘这事儿有问题’的表情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所以太后给了她一个警告的目光,然后又对魏余欢道:“你回去劝劝鸿烈,让他仔细想想,在他心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重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重要。让他想清楚了之后,自己去给皇帝上折子,该请罪请罪,至于具体该怎么说,他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儿。”
皇后益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了。既然是顶撞了太后,那为什么不给太后请罪,而要给皇帝上折子?而且,为什么要问‘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重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重要’?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重要还是温庄和重要’?太后这番话说得似是而非,仿佛是在指着温庄和,但又仿佛带着某种只有她、皇帝和鸿烈能听懂的暗示。
这个朝堂越来越难以捉摸,还好父亲已经归乡养老,哥哥也只在翰林院编书……皇后第一次如此佩服父亲当年的远见。
“母后,那儿媳也告退了。”看着太后打发走了魏余欢,却没说任何让自己走的话,皇后坐了一会儿之后还是有些呆不住了,就想主动离开。
但太后显然不打算让她得逞,“皇后别急着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太后终于发话了,虽然她说的并不是皇后想听到的那句。
皇后无奈,只得老老实实地答一声儿是。太后沉吟片刻,“你父亲当年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
听太后提及已经荣休多年的父亲,皇后的右眼皮狠狠跳了一下。便只听太后又道:“你父亲当年说,既然不打算杀了温家兄妹,那就只能留下温家。否则,其他的任何选择都可能导致无穷无尽的祸患。当时,我和皇帝都觉得你父亲夸大其词,只是因为要保温家那兄妹二人才想出来这样的瞎话。但现在……我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但我已经信了。”
皇后没有说太后英明,也没有说太后多虑,她只是迟疑了片刻,然后低声道:“令圣人担忧,是温家兄妹之死罪。”
她的父亲柳桥当年就差点儿被人扣上温党的帽子,如今……她怕旧事重提,怕被迁怒。尤其是在这个柳桥一语成谶,温庄和果然给鸿烈造成了麻烦的时候。
“你父亲当年都说对了,只怪我们谁都听不进去。”太后没有理会皇后的话,“我现在真后悔当年一时心软,让皇帝放这兄妹俩一条生路……这哪里是给太子和社稷积福?这根本就是留存祸胎!”
皇后益发低下了头。太后此时也许并不需要一个人来劝解,她只需要一个人来听她泄愤。她恨温庄和的心,就如同她恨当年的自己多劝说了皇帝一句一样。
这对兄弟毁了温庄和的家,温庄和如今就反过头来要害他们的家。皇后心想,果然是报应不爽。
“皇后,给你父亲写封信罢,就说是我想请他回京一趟。温家蒙他之恩,他也对温家颇多了解,也许这次只有他能帮帮鸿烈了。”
皇后心中一震,口中虽然称是,但却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父亲真的回来趟这个浑水。
所以当晚,皇后便将‘承母后慈命写与家父的信’交给皇帝御览。皇帝默默地看完了信,又问了一遍当时太后的说法,然后才对皇后道:“既然是母后慈命,那就让人抓紧送出去罢。不要耽误了。”他顿了一下,对李富道:“太子近来的功课都做得很好,让人去把那方新进上来的端砚赏到东宫去罢。”
虽然皇后的本意是希望皇帝能说出不让她送信的话来,但转念一想,皇后自己也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毕竟,皇帝和太后现在没什么矛盾,而且太后让柳桥来的理由也算是光明正大,皇帝也不可能说‘朕没打算让人查清楚鸿烈一事,因此不必让柳老大人来了’。这么一想,皇后也就只好暂时把将自己父亲从这滩浑水里摘出去的心思放下,笑着谢了恩。她明白,皇帝这是在赏太子,但实际上也就是在奖赏她的毫无隐瞒和坦诚相对。
有一个好消息,也算是好的。皇后这样安慰自己。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城门打开,皇后命人把书信送出城之后不久——准确地说是当天夜里,就有襄王府的人连夜至宫门求见。
在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前来之后,皇后清楚地听见自己心里有一个雀跃的声音在叫喊着,只要襄王不幸……那父亲他就可以确保全身而退了。
因为,襄王府的人带来的不是襄王的请罪折子。
而是,襄王穆鸿烈遇刺受伤的消息。
作者有话要说: 死不了
东主是要写三角恋和玛丽苏的好作者
☆、死牢中
当郑嘉树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驿站已经被禁军包围的时候,温庄和早就被当作凶嫌扔进了刑部大牢。温端成父女之所以能幸免于难,还是因为温庄和对去抓她的刑部官员说了一句,“我哥哥与此无关,你们带他和我侄女去驿站关起来也就罢了,反正有我在,你们也就可以交差了。”
刑部官员本来是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句鬼话就放了温端成父女的,但温庄和之后的一句话又打消了他拒绝她的念头,“你们的陛下让你们带温庄和入狱,但还没让你们带温庄和的尸骨入土罢?”
原本戴在她高髻上的那支累丝云凤纹金簪[1]异常尖锐的簪尾,正抵在她脆弱的脖子上,那官员甚至已经看见细小的血珠从簪子抵着的地方,一点点沁了出来。
说白了就是吓傻了,所以糊里八涂地就答应把温端成父女关在驿站而非刑部大牢——皇帝在听奏报时,是这么总结的。
皇帝顺手罚了那官员三个月的俸禄,但却无意让人把温端成父女从驿站带出来投入大牢。
因为皇帝认为这种行为既没必要,也缺乏理智。首先,驿站还是在京城,又有重兵把守,温端成带着一个幼女,根本逃不出来。其次,郑嘉树还住在驿站,朝廷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嘉树和刺杀行动有关,既然如此,那么朝廷也就有必要给他留面子——比如,不把他带来京城的人从他眼皮子底下带走,送进大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因为温端成而让两国伤了和气。
不错,他并没有输掉上一场战争,但上一次没输,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信心还能赢得下一次。
而且即使赢了又怎么样呢?战争对参战双方来讲都是消耗,皇帝并不希望在一口气没缓上来的时候就开启下一次。
不过皇帝不知道,其实郑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