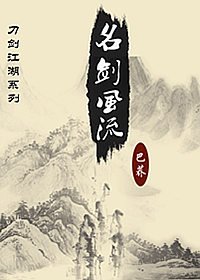富贵风流-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郑嘉树似乎有些意外,他想了一会儿,“是么?温家如果有这样的杀手锏,又为何这些年来沦落至此呢?”
“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国主能放心那么重要的东西,攥在一个随风倒不讲忠诚的商贾手里。所以随着那样东西越来越重要,我们也就越来越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即使我们当年没依仗此物去讨要什么身份地位,也一样会有类似的下场。不过假如我哥哥没把我许给一个梁国人,那也许这样的命运会来的迟一点儿。”
郑嘉树突然意识到那样东西是什么了,他脸色一变,“你居然将图纸交给了襄王?”他怒道:“光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温庄和并不怕这样的宣言,她甚至还更挺直了身姿,“郑大人自己傻,可别以为天下人就都傻!我为什么要把图纸给襄王?让他也好过河拆桥么?那是我最要紧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双手奉给别人呢?我给他的是找到温家这图纸的地图,只要他是真心想着我,他就一定能找到那图纸。郑大人,你不怕我温庄和,那你怕不怕吴国造出来比他们这次战争中用的更强大十倍的火炮?你怕不怕他们造出来的这种炮可以让梁国士兵血溅三尺,尸骨如山?你要是怕,就得留着我,留着我哥哥,好让我们把这件灭梁国的利器变成杀襄王的匕首。”
“但如果他已经找到那些图纸了呢?”郑嘉树面目狰狞,一张原本俊秀的面孔几乎扭曲成了恶鬼。
“他一定没有!而且即使他找到了,他现在一时也做不出那样东西。因为他现在手上还少一个能看懂那些图纸的匠人。但如果您杀了我或者我哥哥,那就没有人能挽回这件事了。您知道的,这世上总不缺一两个天才,谁知道哪天就让穆鸿烈找到另一个能读懂图纸的人了?”
郑嘉树这个时候反而冷静了下来,他看了一眼那不知所措的侍卫,摆摆手示意那人退下,然后对温庄和道:“那你打算怎么挽回这件事儿呢?”
“我会用这些东西让穆鸿烈兄弟阋墙,万劫不复。”
作者有话要说: 人家写感情戏都手到擒来,东主写就是吭吭唧唧拖来拖去,第一部分剧情都进展了一半了,感情线居然还没推上来!!!!!!
东主先出去跑两圈,大家勿念[谁念你!!!
☆、最爱物
“什么?郑嘉树没把温端成抓起来?”苏鹤亭皱眉问道。那家丁说了声是,苏鹤亭眉头紧锁,挥挥手让他下去了,“白兄,看来咱们这一出儿唱砸了。”
白南山摸摸自己的胡子,叹了口气,“真没想到郑大人如此糊涂啊。”
苏鹤亭摇摇头,又叹又笑,“白兄这么说可就是不了解郑嘉树此人了。这位郑大人虽然是正经王室贵戚,得国主爱重,但毕竟是久居高位,朝野内外不知有多少人嫉恨他。不过任凭多少人嫉恨,偏偏就是从没有人能扳倒他。这可不是运气。这是本事啊……白兄,郑嘉树这个人不是个傻子,他即使知道温家眼下有用,也不会看不清咱们俩家的重要。他没按着咱们的意思走,要么证明温家摆出了让他不得不更重视的理由,要么就证明他不想让咱们得逞,不想向咱们示好。”
“那贤弟认为是哪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呢?”
“前者更有可能。郑嘉树此人没必要为了一时证明自己不上当就放弃这么个示好的机会。而且按着咱们之前看到的情形,分明温家这兄妹俩已经是捏在他手心儿里了,他完全没必要再顾及他们什么。所以向咱们示好原本应该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儿,于他没半分影响。但他没这么做,就说明温家拿出了什么东西,让他必须让步。”
白南山不认识郑嘉树,但他却和温端成打过交道,“温端成虽然算不上什么贤德之人,但也算是个方正君子。如果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救命法子,那十有八九也是温庄和这个妮子出的。”他顿了顿,“这个丫头啊,如果一次打不死她,她以后只怕就能变出无数花样来报复我们。”
岐黄堂和温家这种做杂货生意的商人没什么来往,苏鹤亭也只是听人议论过几句温庄和,在他印象里几乎所有人都说温庄和是个无知娇纵的丫头,“温庄和不过是个女流之辈,能有什么本事?”
“贤弟,没本事的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杀夫求荣的毒妇的。当年她被当作是无知之人,是因为温家不需要她做太多,但不做不意味着她不会做。”白南山突然压低了声音,“贤弟,为了咱们两家以后着想,温家这兄妹俩已经是不得不除了。”
苏鹤亭似乎笑了一下,轻声问道:“那白兄看,咱们该怎么办呢?”
——————————————————————————————————————————
鸿烈是因为家仆回报侧妃见到了温端成,才知道魏余欢去了温家祖宅。他心里疑惑,魏余欢和温庄和即使当年真的有点儿交情,那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想起来去故友的老宅看看,偏偏这个时候想起来了?不过他倒不是怀疑魏余欢和温端成有什么私约——一来,虽然当年二人有过口头婚约,但毕竟当时魏余欢还小,又过了这么多年了,没道理突然就旧情复燃;二来作为襄王侧妃,魏余欢身边时时刻刻都有许多仆婢,真要说私通款曲……也不可能。所以他只是疑惑魏余欢到底为什么要去温家老宅。
“余欢,你跟了也快我十年了,你就是这王府实际的女主人,也是我身边儿位分最尊的女人,你我之间,形同夫妻,你没什么话不能跟我说。所以现在,你告诉我,你去温家老宅干什么了?”
魏余欢脸色苍白地拧着手里的帕子,半天说不上话来。
鸿烈皱皱眉,看向跪在一边儿的绿蜡,“绿蜡你说,侧妃到温家老宅都去了哪儿了?”
绿蜡偷偷看了看魏余欢,想了半天到底不愿意出卖自己家小姐,便只是磕头不肯说话。鸿烈看着腻烦,便叫来等在一边儿的两个粗壮仆妇,冷冷的道:“把她拖出去,打到说为止,如果一直不说,就打死了算罢。”
那两个仆妇虽然也有些不忍心看着绿蜡这样一个瘦瘦弱弱的丫鬟做了王爷的出气筒,但她们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仆妇罢了,只有听主子吩咐的份儿,而没有跟王爷这儿多嘴的道理。但其中一个也是好心些,大着胆子劝了绿蜡一句,“姑娘,说了罢,何必受那个皮肉之苦呢?”
到最后卖了侧妃,也挨了打,反而两边都落不了好儿,还不如干干脆脆地得罪一边儿,讨好另一边儿呢。
绿蜡也怕,但她看看魏余欢,最终还是咬紧了牙关,一个字都不肯说。鸿烈冷笑了一声儿,“我府上有这么个忠仆,我以前竟然都不知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拖出去好好赏她?”
那两个仆妇再也不敢多嘴,忙领命就要将绿蜡拖出去。
“住手!”魏余欢还是出声儿制止了。她跪倒在鸿烈脚边,“王爷,我说……您放了绿蜡罢,跟她没关系。”
鸿烈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儿,“那你说啊。”
“妾……妾去了湖心亭。”魏余欢身子还有些发抖,她没等鸿烈问为什么去湖心亭,便道:“妾是想起来旧日里跟温家姐姐作伴的光景,又想起如今大家立场不同,实在心里伤感……所以才……”
鸿烈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倒好像是从来都不认识她一样,“是么?”鸿烈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原来是念起过去的好儿了啊?不过余欢,你到底是想起来过去两个人做伴儿的日子了呢,还是想起你们魏家盛极一时的日子了呢?或者……两个是一起想的?”
魏家的发家史并没有那么光辉,相反,这种兴起充满了投机倒把和赌博。
魏家当年也是商贾,但其家业不但比不上温家,甚至都比不了苏、白这样的人家。但就在梁吴二国分立的时候,魏家先人将全部的赌注都放在了吴国这一边,他们捐出了几乎全部的家产,换得了战乱中吴国开国之主册封的爵位——还好,吴国虽然没大获全胜,但也不算失败了。而魏家则经过这么一出儿之后,成功上位。
不管正经的官宦人家是否就觉得魏家矮他们一头,反正相对于更多的仍旧属于底层,只能任人鱼肉的商贾来说,魏家赌赢了。不但如此,在放弃经商之后,魏家还竭力和温家交好,并借着温家的财力在近二三十年里扶摇直上,甚至一度位极人臣——直到十年前,随着温端成一脉一夜之间的败落,魏家也渐失君心。
“余欢,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还想听你讲呢。你到底,想起的是什么呢?”
魏余欢身子颤抖,却不知为什么,凭着直觉就觉得自己绝对不能说出那幅树下美人图的事儿。因为直觉告诉她,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带来她和整个魏家都无法承受的后果。
鸿烈的手指扣着椅子扶手,神色渐渐不耐烦起来,他皱着眉看着刚刚捡回一条命来,尚且惊魂未定的绿蜡,“怎么样?你主子不肯说,你说不说?到了这地步了,你们还想瞒我什么?是不是真要我给你们治一个里通外国的罪,然后丢到刑部大牢去才肯说实话?”
绿蜡带着些恳求的看着魏余欢,“侧妃……您说罢……”也许说了,反而是给自己留余地呢。她心道。
魏余欢咬着嘴唇,许久才颤颤巍巍地道:“妾……是去看那架树下美人屏风的。因为……因为温家姐姐当日放在那个镶金粟的盒子里的东西,并不是一对儿孔雀簪子,而是……”她不知怎么竟流下泪来,“而是一幅和那屏风上一模一样的树下美人图……”
鸿烈先是一皱眉,似乎完全没想到那幅树下美人图能有什么问题。但只是片刻之后,他突然睁大了眼睛,猛然站了起来。
——————————————————————————————————————————
“你最喜欢的就是我罢?”鸿烈靠近温庄和,嗅着她发上淡淡的玫瑰香,嬉皮笑脸地问了一句。
温庄和笑吟吟地退开了一步,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不是。我最喜欢的偏偏就不是你。”
“你不喜欢我还能喜欢谁呢?难不成这世上还有哪个人比我对你还好么?”鸿烈跟上去一步,一句反问看似是责备,但实际上却没有丝毫的担心。
“我呢,最喜欢的是我家湖心亭里那架六扇的树下美人屏风。”
“一个死物罢了,有什么趣儿呢?怎么比得上我能对你好,能陪你说说笑笑,打发时间?”
“它是死物,但也是我的命根子,是我们温家的宝贝。你虽然对我好,但未必就真的能如你所说的那样一辈子对我好。万一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也还能有它。你说,它是不是对我好?”
作者有话要说: “什么?郑嘉树没把温端成抓起来?”苏鹤亭皱眉问道。那家丁说了声是,苏鹤亭眉头紧锁,挥挥手让他下去了,“白兄,看来咱们这一出儿唱砸了。”
白南山摸摸自己的胡子,叹了口气,“真没想到郑大人如此糊涂啊。”
苏鹤亭摇摇头,又叹又笑,“白兄这么说可就是不了解郑嘉树此人了。这位郑大人虽然是正经王室贵戚,得国主爱重,但毕竟是久居高位,朝野内外不知有多少人嫉恨他。不过任凭多少人嫉恨,偏偏就是从没有人能扳倒他。这可不是运气。这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