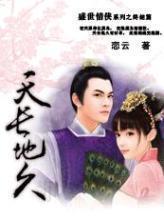天长久词-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那些公差没个敢说实话,只赞不绝口。于是,吃了又吃,苦不堪言。”
和尚听闻一笑,花红玉道:“另一癖,杜慎好种葫芦,不说他私宅如何,光是衙门的门庭外墙,皆被他命人种满,累累如贯珠,倒是清香无比。
听闻那公堂壁上,亦被他挥毫,画上水墨葫芦无数。此外,他还写了一本六卷《葫芦谱》。”
和尚愈听愈奇,拍膝笑道:“想这杜公定是个奇人。”
花红玉也浅笑,谈得兴尽,用罢肴馔,见时候不早,便命丫头银儿收拾两间舱房,请宗师、阿沅歇息。
是夜,湖上华灯初上,兰麝香气,火树炫金,银花蓬簇。
隔着湖面,那席上饮酒作乐之声,彻夜不歇。
阿沅不能睡着,倚在床头,从这舱房极窄小的明窗,望得虹桥湖上凝碧,四桥涟漪处,有夜色里潋滟的清波,卧了满腹的星辰,那等流光溢彩。
还有一艘艘画舫,拂动的珠帘,映灯的绿窗,挨得近时,透来一阵阵衣香,一绢绢花笑。
阿沅一恍惚,似闻见那衣香同室,看见那花笑在眼前,似梦似幻。
只听湖上一位豪客啸叹,道:“若不是大寒天气,这湖上没有一日是冷清的!虹桥之盛,可比银河,怎较秦淮小哉!”
原来,扬州人常道:“虹桥水号小秦淮,盖与金陵相较而逊焉者也。”
阿沅去过金陵秦淮河。此处水光,与之相比,并无逊色。惟是此名,起得气短。
阿沅微微一笑,扬州城怎那许多文章宿老、风流才士都不睡,专来此夜游哩?
此夜过得既漫长,又迅疾,阿沅手上玩着四枚珍珠,戏法一般摩弄,时隐时现,那珍珠愈暖,她心上愈淡,湖上便渐渐散彻了万点星光,清冷了一轮月色。
天光渐青,人声渐懒,阿沅也终于讨得清静,朦胧睡去。
等阿沅醒来,已过正午。银儿敲着门,端来热水给她洗漱。阿沅洗完脸,银儿给她梳头,上妆。
妆罢,阿沅对着镜子,道:“卖俏吓和尚一番,也不错。”
珠儿听了直笑。
却说,和尚正在舱底用些午饭。阿沅进来,盘腿坐上,早午饭并用。
和尚初初没在意,无意一抬头,见阿沅打扮得好似万紫千红满园春,大异平时,不免噎住,半天咽下,喉头滚了滚,道:“阿沅你这是……这是?”
阿沅道:“兴之所致,偶尔为之。”
和尚一笑,道:“美得很,美得很,和尚险些认不出你来!啧啧,只是这等妆扮一新,只对着和尚,岂不浪费?不如去筱园打打秋风,包管迷倒他家的少主。”
阿沅道,“谢无忧撒下的三百两银子,还不够和尚使的?”
和尚道:“阿弥陀佛,我只盼拣着一个聚宝盆,财又生财呢!也罢,也罢,檀越你不肯去打秋风,便将那四枚珍珠交给和尚,和尚让银儿上趟当铺,少说也得换回几十两银子。”
阿沅不肯,只道:“和尚你钻进铜钱眼里爬不出来,有失宗师风范。”
和尚道:“我这是为咱们白马寺计长远,你哪里晓得我的苦心?”
阿沅但笑不语,埋头吃饭。
不多时,花红玉已从衙署大街坐马车回来,乘小舟登上画舫,下舱,掀帘,笑道:“今日这案子审得也葫芦。”
“怎么葫芦?”和尚问道。
花红玉这会坐在妆台边,有小婢巧儿,替她脱去外衣。她笑道:“杜知府坐堂审案,先是命公人抬来萧进的无头腐尸,又端来冰匣盛好的人头,再用一个木盘,盛上血字细绢。
三样皆备,通传了扫垢山庄谢家,还有那洛阳天下门来的沈冲,今早也到了扬州城,传上了公堂。”
和尚沉吟道:“武林当世的两大名门,公堂对簿,非比寻常,只是这沈冲为人如何,小玉可看出端倪?”
此时银儿递上茶盏,花红玉接过,道:“宗师莫急,容我与你细细道来。”
作者有话要说:
☆、判官震邪
花红玉啜饮那茶,银儿撤下胡床上的饭桌,捧上新茶,巧儿点了一炉佛手香。
花红玉款款一笑,道:“这杜州官也怪哉,大早上,百姓人挨人看他审案,他却像董子祠坡下、大东门书场的说书先生,卖起关子。
众目睽睽,只听他吩咐嫡亲的方师爷,将数月内,他在扬州城治鬼的功绩逐一宣读。”
花红玉话一顿,道:“这杜知府当真是别出心裁,试问,朝廷考评官声,何曾命百官呈上治鬼的功绩?”
飘瓦、阿沅听了皆是稀奇。
花红玉道:“这方师爷念足半个时辰,那杜知府面有喜色,好不得意。”
阿沅摇头,问道:“他治死几个得道的怪,这般喜不自抑?”
花红玉浅笑道:“多不胜数,当中有两个法力高强的。一个是虎头关的鼋怪,晴天浮上水面曝背,冬日水涸,化为针线婆,四处向人讨生肉片,不予她,她即要吃人。
方师爷奉知府之命,派了差人在虎头关水深处,以大块生肉作饵,大网拦截。
夜里,果然抓得一只鼋怪,已送至天宁寺,令众僧好生念经感化它。”
阿沅忍俊不禁,又问:“那另一个怪又如何?”
花红玉道:“另一怪,则是城内贞节牌坊对过的乌墙上,生长了青白二色的两根何首乌藤。
传闻每至月夜,那何首乌便要化作两个小儿,冉冉而下。遇上街里孤身的妇人,无不牵衣而哭,只道迷途。
那妇人若是心肠一软,送这两个小儿归家,往往失其踪迹。杜知府听说此怪,亦派师爷出马,大张旗鼓,掘开那何首乌藤,当众用铡刀凌迟。”
和尚听了,笑而不语,如有会心。
阿沅不解,问道:“和尚笑得古怪,有什么话瞒着不说?”
和尚啧啧道:“世上哪这许多怪?”
花红玉笑道:“妹妹有所不知,鼋怪一事,着实是丰乐巷的一个馋肉的婆子,装神弄鬼,专挑夜里天黑,上街骗肉,煮着自吃。
杜慎治了那鼋,敲山震虎。她没了名头,不敢作怪,也算受杜知府一戒。
至于那何首乌藤,不过是几个大胆的人贩子,只将蓄养的乞儿,打扮齐整,再令其哭于道中,引得心善的妇人,陷入罗网。
这伙人妄想避开官府的追究,这才编出一段瞎话。”
阿沅听了明白,道:“看来,这杜老爷当堂宣读治怪的功绩,是要震慑邪道。”
和尚赞道:“鬼面判官杜公,当真妙不可言!”
此时,花红玉低头饮一口茶,又吩咐银儿将茶杯撤下,为宗师与阿沅换上一轮新茶。
“看他审案子,却深不可测。”花红玉道。
“怎么个审法?”阿沅问道。
花红玉道:“杜知府先问那沈冲,可知萧进为何孤身一人来到扬州?那沈冲生得头脸方正,浓眉大眼,声音也洪亮,只答不知。
杜知府又问他可曾在洛阳见过萧进?
沈冲只答半年前,萧进曾向天下门老门主段枭,请辞,说要金盆洗手。他家门主本不答应,但萧进执意要走。老门主也无可奈何,只得办一场送别宴席,又赠他丰厚金银。
此后,萧进就已离了天下门,不知所踪。”
和尚听到此处,问道:“听闻那萧进的包袱空荡荡,并无金银。难道老江湖也着了江湖诡道,被宵小劫了财,灭了口?”
花红玉道:“杜知府也是这般问,但沈冲只道不知。杜知府没法子,只好又审那谢家大总管谢忠。
谢忠更是不知,虽说扫垢山庄与天下门都是江湖赫赫有名的世家,但天下门远在洛阳,非是大小节红白喜事,扫垢山庄与其往来甚少。
谢忠更是口口声声言明,谢家不曾结纳这惊雷剑萧进。
杜知府听到此,笑道,这萧进也奇,金银不在身畔也罢,连惯用的惊雷剑也不在,莫不是都沉进河里去?
杜老爷便又审那船老大郑老四。郑老四是老实人,道,当日船重,在水深处下货,小船大船地走。船上许多船工,个个忙得不可开交,没人见到金银包袱。”
和尚道:“这可真是一问三不知,那杜知府审不下去,又要如何?”
花红玉道:“杜知府呀,叹叹气,拍三下惊堂木,断言抛头的犯人正是萧进!
此言一出,百姓无不哗然。
杜知府又笑道,这萧进本是人杰,死后自是鬼雄,怎甘心无名无姓,埋于荒野?故而生魂作祟,割下自己的头,飘来飘去,惊吓妇孺!着实该罚!
但这死人既无钱财,自是亲信要受牵连。是而,杜慎判沈冲出些银钱,安抚当日影园受惊之人,并命他将尸首领回,好生安葬。
至于扫垢山庄所受的牵连,定是因为这萧进死后,怨恨谢家既同为武林中人,怎这等粗心大意,不晓得一代豪杰死在码头,有失人情!是而萧进做鬼亦要拖谢家人入水。”
这一番话,和尚听得目瞪口呆,阿沅也摇头道:“果然断得一桩葫芦好案!”
此时,花红玉微微一笑,又讲道:“杜知府这般敷衍了事,便要退堂。那沈冲自是不肯,说兄长死得蹊跷!谢家人,也不肯,说惊雷剑好男儿,不该含冤不白!
杜知府又是叹气,又是摇头!
此时,幸而李都头带着公差,从衙门外挤进公堂,启禀了杜知府,说他找着了萧进在扬州城的私宅。
听闻,那宅子建得又精细,又清静,想是萧进退隐定居之用。”
和尚道:“原来这萧进并非路过扬州。”
阿沅道:“杜慎是故意试探谢忠与沈冲罢,若他俩一心结案,定有心虚之处。”
和尚点头称是,又问道:“那萧进的宅子,又是怎么个情形?”
花红玉啜口热茶,道:“扬州城里有一个典卖宅子的老掮客,叫詹光的,在城门见得萧进的人头画像,认得是一年前买下兴教寺街一座大宅的主顾。
詹光到了衙门,一五一十禀了知府老爷,说这萧进出手阔绰,买宅子是为了娶老婆。”
“萧进的老婆住在扬州城?”和尚一听,更奇。
花红玉微微一笑,道:“正是,那老掮客认得萧进的妻子,正是这小秦淮的俞婉儿。那俞婉儿相貌生得十分标致,但她性子烈,又爱讹客人的钱财,没有一个客人做得长久。
那詹光自然晓得俞婉的名声,是而也奇,还说这俞婉儿,寻常人家娶她作妾,都嫌扎手,怎有像萧进一样相貌堂堂、磊落大方的好男子,娶她做正室?”
此时,花红玉道:“这也难怪那詹光心疑。依妾身这几年,眼里见得,青楼女子若想做富家公子的正室,少有如愿的。”
此时银儿也插嘴道:“姑娘说得不错,那白四娘和赵红官,就是两例。”
花红玉道:“不过,这也是我等的世俗之见。想来这惊雷剑萧进,不是俗人。
一年前,我也曾听说有人给俞婉赎了身,但她的妈妈郑姑嘴严,只说她嫁给镇江的富户,何曾想到她还在扬州?
想来她也是极爱慕那萧进,是而改过性子,大门不迈,二门不出。不然怎会一点消息也不透?
那詹光也说,这萧进极其宠爱俞婉,买下宅子后,不但置办贵重家具,还请那做首饰的几个银匠、做家常衣裳的几个裁缝,将嫁娶的妆奁,都办得齐齐整整。
花红玉说得清淡。
但她也晓得,世间少有这般男子,对一个风尘女子,也肯用情至既往不咎,珍重至许以白头。
此时,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