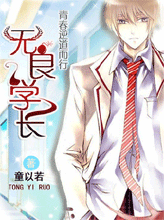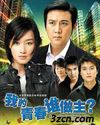�ഺ��̳-��2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һ�治ͣ�������һ�治ʱ��һ����塣�����������ſ�ڵ��ϣ���ڴ�ڵش��Ŵ���ʱ����Ȼ��������ʱ����������֧��
��ͻȻ���»�ǹ�������������һ�����˵أ���������ëת�����ܡ�
���е��˶�����һ�ٶ������ˣ�������ٻ��е���������������ˣ���
�ô˻���������һ����Աƴ�����һ������Ҳ���ũ���������������Ǻ�ˮ�����࣬����ɹ�ù��̵ĵ��ϲ�ͣ�ش�ڴ��Ŵ�������ٻ�������ΪЦ��
����Ͻ���ȥ������ϵ�������¡�
ʯ�ִ塢�����ͳ��ξ���������������������һ���š����¡�
ʯ�ִ���ʳָ����һ�½����۾�������һЦ������������ǹ���Ҿ�֪�����鲻��ء����ʵ�ֶ���������˾��ռ���ˣ��绰����Ҳ��ͨ����ѧ�������ﳵ����֪ͨ����������һ��С���������ţ�������ֱ��λ������Ҳ�����������Ҿ����˵�����һ���š�ȥ����˾����DZ�Ҳ�������ˣ����ǰ���������ˡ���
�����첻���ع������ͷͷ������ǵ����ʴ���̵�Ӫ����������˵��
ʯ�ִ�Ц������Ӫ������ô�����ܵ�ǹ���룿��˾��˵�����DZߴ����ˣ����Ϲ�����Ӧ���ǡ�����ǹ���жϣ�����˾��α������ص���սУ����˾��ũУ��ʦ���⼸��ѧУ����Ϊ����ũ��������������ѧУ����ѧ����������һ��Ҫ�����ǽ�Ӧ��������Ȼ����ʹ��˳����ˡ���
������Ҫ����ũ������ս�����Ԯ�֣���������Ҫ�Դ���ˡ�����建��������Ҳ����������һ�����ж�������֪��ʦ���ĺ���DZߵ������ô���ˡ���
ʯ�ִ���ܵ�������˾�����µ��˶������������ѧ�����Ѿ��ż��ˣ����������Ǹ����˾���ظ㲻��Ҫ�Կ����ղŵõ���Ϣ��ũУ������ɽ�����������ˣ�һ���ӵ����Ŵ����ϴ����������յ�����û�����ż�����û�д����ӣ����ڱ��ͽ�ҽԺ����ȥ�ˡ���
ʯ�ִ����ڽ��������������һ���ŵ���˾����Ŵ����������ƺƵ����ĸ�����Ԯ��
������غʹ�����֣������٩��������λ��������ѽ������Ϊ�����Ѿ������κ����ء���
ʯ�ִ�Ц����һ�䣺������������������ڻ�����Ц����
��˾������������������࣬������ʵ��������Ƕ��굽����ȥ�ˣ���ø����һ������
��������˵�������ǴӺ������������ͻΧ�ģ�Ҫ�����������������ӣ������ȫ���ˡ�������ͻΧ�ľ�������˵��һ�¡�
��˾�����˺������Ц�������ǵô�ǰ��ĭ����˽��ʱ��ͬѧȥ͵���ӣ�����������������һ�������������������Բ�������Ҫ���������ǡ���ҹ͵���깷����֪��˭������ĭ���������ѿڶ������������۹��ض����ҡ���������˾���궴ͻΧ����Ҳ��һ��������������ͻΧ�꺭�����ҽ��ҡ���˭������������
ʯ�ִ�������˵�������¶�ʮ�������Ǵ�������˾���������ǻع�ͷ���ִ����ǣ�������ԩԩ�౨��ʱ���ˣ��Ժ������ѵ��ճ��������������������������������κ��κΣ�����
�������ԣ����ƴ�Ц���������ԡ���
�зֽ̣�
��ٷ����ƻ��ǣ��������ʵ���ꡣ
������·����ȥ���ϴ�˷��ϳ���
���ǣ�һ�������������ˣ�����������ۿ�������
��֪������Σ������»طֽ⡣
�ڶ�ʮ���ء���������������ˮһ����
�ڶ�ʮ����
��������������ˮһ����
���κ���˾��ǹ�������
��˵һ��������ʮ���¶�ʮ���գ��������ձ���������ëZD���������ָʾ����֪ʶ���굽ũ��ȥ������ƶ����ũ���ٽ��������б�Ҫ��Ҫ˵������ĸɲ��������ˣ����Լ����С����С���ѧ��ҵ����Ů�͵�����ȥ����һ����Ա������ũ���ͬ־��Ӧ����ӭ����ȥ����
������ʮ���¶�ʮ���ա������ձ����ַ�������˵����Ը�ⲻԸ����ɽ���磬�߲����빤ũ���ϵĵ�·�����Ҳ�����ëZX����·�ߵĴ����⡣��
�˺�����ƪ��빷�������ëZDһ�������귢���ġ������˶��ķ���һ������˵�Ļ����������Ļ����Ļ�Ge����֪ʶ���ӵ����ķֽ磬�����Ƿ�Ը�Ⲣ��ʵ�к�ũ�������ϡ������Դ�Ϊ�ݣ���ȥ��ȥũ�壬�����ж�һ�������������Ψһ�����������˲����������ǣ��ѵ�����ũ��ȥ�ᵽ�����ͷ�Ge���ĸ߶ȡ�����һ���������Ƿ�Ը�⡢���Ļ��Ǽ��⣬ũ��ͳ���֪ʶ����Ψһ�Ĺ��ޡ�
�Ӵ��Ժ�ʮ��֮�õ���ɽ�����˶�����������Ļ��
����������������������ӿ�ֳ���������Ⱥ�壬��ΪëZD�����˵����й���̳���Ż���ɨ������������Q����СP����������Zhen������Qing��½��Yi������Kuen����Long��һ�����������쵼���Ժ��䱾��Ҳ��ͬһ�鰹��IJ���������Ĩ���������DZ�������һǻ�����������Ѫ��������ͳ�����ȹ̵Ľ�ɽ���ֱ�ͳ���ߺ�����ϧ����������˳�������ˡ����ǵ��ഺ���ӵ���������ı߽���ɽ����ƽԭ���ӹȵ�����ͷ���Ȳ���Ը�ء����ܡ��Ÿ���Ԩ��һ������ʫ��ġ���⡱��������һ�Դ��ɸ����ˡ�
�����������������������丳�����ǵ���ʷʹ����
�˺�ʮ��½����һǧ���ٶ���֪ʶ������뵽��ɽ�����˶���ȥ��ֱ��һ���߰����ⳡ��������������ǡ�ȫ�����һ�����־�����ڡ��������ޡ�����֪ʶ���ꡱ��һȺ�˴�������Ѫ��ļ����������Գƺ�����Զ�������������ʷ����֮�С�
��Ȼ�������е��˶���������ɽ��������·��
��塢ۢ����ͳ��ξ�����������ײξ����ˡ�
��Ϊ��������ٻ������ﲻ��Ӧ���ҵ�����ֻص�ѧУ�μӡ������ָ������ˡ�
���ϴ��һ�֪���˾�����ˣ���������64���·ŵ�֪�࣬������Ȼ���ֻص������ij����ؼ�����������
��ʱ�����췴�ɺ͵�Ȩ�ɵġ������ڡ���Ϊ����ʱ����һ�·��ϴ����ﻹ������Ϊ�����¹����ί�ḱ���Ρ�
�����ϴ��Ǹ����۲��ص����֣�������һ�仰�����ҲŲ�ͼ�����ί�ḱ��������������˴�����ү��������ү�������Ӿ���ѧ�ν��ó�͢�а�������Ǻ����Ϳ�������ˣ��ˣ��������ɣ�����Ϊһ���Ȳ��п��ֲ����õ�СС��ɴñ���ۣ���Ҫ�IJ��ǵ��٣���ֻҪ���˵����ϡ��±������ɣ��������⣬����
���Ǻ������ظ�ί�᳣ί�������ί�ḱ����һ�����˸��ɸɾ������ֻص�����ȥ��С���������������š����оƽ�����������Ǯ�����ǡ�����ң���ڵĿ������
������������ʮ����ƶ����ֻҪ��ԭ����֪���˾�����ϲ�����ʲô�������������������������в��������������Ѱ�æ���������ڳ����϶�û�¶ٵ�����£�������ծ��ծҲ��һŵǧ���������ں��ݳ������Ե�Ϳڱ����ѡ���Ȼһ��������ʲô���ֵ��£�����Ҳ�������ԥ��Ϊ����æ����������Ǻ��ݳ�����ϴ�ֻ�����ֶ���һ��˾���ͷ�ζ��ѡ�
�տ�ʼ�ص�����ʱ�������ȸɵĻ��ǵ���ͷ������������е�����ν�����¾��ǰѴ��ϵĻ���ᵽ���ϣ��Ի�ȡ���˷ѡ�
���������ص���ͷ�����ǰ��˹�˾��һͳ���£�ֻ���ɹ�˾�Ĺ��˻����װж����κ������˶����ܲ�����Щҵ�����ǻʵ���������Ҳ���С������ϴ��ں��ݵ�����̫���Һ��ݰ��˹�˾Ҳ�ǡ�����˾�����µij�Ա����˾һ�������Ƿ��ϴ�������ǣ����Է��ϴ�����������ͷ������һ�ݿ�����Դ����������⣬ֻҪ����Ǯ���С�
���ֿ�����Ǯ���Գа���ʽ���еģ��ȷ�˵����һ��ʯ�ӣ�������һ�ٶ֣������˰���һ���������������ð��˷Ѻ�ж��ʱ�䣬�����ϰ�Ͱѹ�Ǯ���㣬������Ƿ��
��ʱ���������Ǯ�ͼ�����ͷ�����ĺ����ѵ��ݵ㼸���ˣ�������ƿ���ʰƣ���������һ�ء�
��ʱ���ݳԷ����˲��࣬�������ݳ�ֻ�����Ҳݡ����ϴ�ȥ����һ�����з�ζ��¥�IJݣ���Ϊ��Ҳ�ʱ����������Ұ��Ұ�á��ڹ����֮���Ұζ������ʱ����������ë�˷�Ǯһ�Ұζ��Ҫ���˺ܶ࣬��ԼֻҪ����ëǮһ�������������ľ�����һ����¾ơ�
��Ȼ��Ǯͨ���Ƿ��ϴ��ͣ��������������Ը�����Ǯ���ͼ���ʱ�䳤��˭Ҳ�������������Ѿ�ϰ���ˡ�������Щ����ʮ�־�������ֻҪ���ϴ����������ϵ�ɽ�»��������ǡ�һ��������ʮ������˹��������죬�����춼��Ϊ�����������
����ǹ����⼸��������������ӣ���·���Ѷ��������������������꣬����������ί�ḱ���ι�ѧ�����ظ�ί�ḱ����Ф���۶�Ҫ���Ե��Ź��ء����ϴ�Ϳ�������٩���������̺ò��д����ͣ�����Ӣ��ͷ��϶�æ��æ�����Ʋˡ�˵�����������Ͽ��ñ�������Ҫ������һ���Ӷ���Ϊ�����Ӷ����ţ���Ϊ�������й�̫��IJ��Һ����裬�������һ���ͷ���������Ӿ��Dz���������
���ܷ��ϵ��ǣ�����Ϊ���˾���ͷ��ʹ���ķ��ϴ���·��Լ���Ge���ڱ�����ʱ����ȫ����ͬ�ն���Ͼ����ǡ�֪���˾����˾�Ҳ�����ظ�ί��ij�ί���������ﲿ���졢ί������һ����λ���쵼�Ǻ���������Ϥ�������ؽ�����˾��ί������κ��չ�����ֻҪ�ǽ�����˾�Ĺ��ط��ϴ����л�ɣ����һ����ŵܷܵ����һ����ֵ���ÿ�춼������������ëǮ�����ĵܷܵ��϶�Ҳ�����Ե����㡢�����������������������ﺫ��Ӣ���ֵ���ÿ����һ���н���ʮԪ�Ĺ�Ǯ�����ú���Ӣ��һ�����������ð�ĸо����������Geǰ�����������������Ѿ��Ǹ��������ˣ���Ҳ���õ����г���ʰ�˼Ҳ�Ҫ���ðײ˰��ӡ��������伢�ˡ�
�зֽ̣�
���оƽ�����������Ǯ�����ǡ�
�����¹ٺ����£��칬������⨺
���ǣ����Һν����ݣ�����Ӯ����������
��֪������Σ������»طֽ⡣
�ڶ�ʮ�Ļء�Ч��ʿ������̸����
�ڶ�ʮ�Ļ�
Ч��ʿ������̸����
����������ѧɳ��
��˵������Ӧ���ҵ������Ӧ���·ţ��������ĸ�ĸ���ǵ�ֱ��λ�ĸɲ����Ѿ���������ʮһ����������߸�Уһ��������һ��ɽ����ȥ�㡰�����ġ������ﻹ��һ���ܵ�����ѧ��Ҫ�չˣ�������������·ŵ����ˣ�ȴ���˸������ʱ���������顣
�������ռ�������ͳͳ������������Ի���������档����������˹ë��������³Ѹ�������⣬������ʮ�������ġ�������������ʷ�����ڸ���ġ�С���������к�ŵ�����ѧ�����Լ��ǵ���˹�ܵġ������ۡ�������Ӳ�С�
����Ҳ�����������ҿ��顣����������ѧ�����ξ���ѧ֮����鲻����Ȥ�����Ƕ���ѧ�������dz�ƫ����
�������ﱾ�����в��ٲ��飬���ϴ���塢��������������飬ʹ����Զ����������ЩС�ֵܡ�
����Ҳ�͵�ֱ���صĸɲ������߸�Уסѧϰ��ȥ�ˡ�
û�и����������Ӿ����������Ҹ������ӣ��������ǣ��������ڵĿ��飬����ĺ����ᄀ�����Σ�������ա��Ժ�����˯�����϶��������ң�������ȫ�ܲ����������������һ�����������������������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