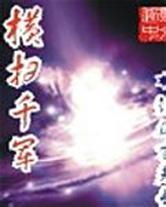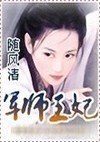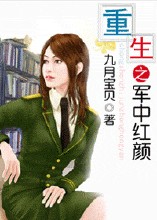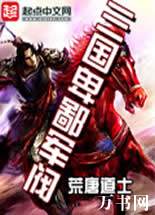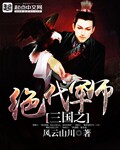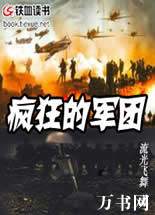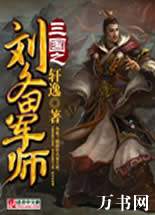施琅大将军-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施琅擒杀曾德是施、郑决裂的直接原因,因而记载颇为详细,各家的记载虽大体相同,又因各自立场有别而不尽一致。
据郑成功的书记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到二十日,郑成功才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宣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从杨英的记载看来,曾德擅离施琅军营,投奔到郑成功帐下,在郑成功答应其请求的情况下,施琅还将其拿回处死,是对主帅郑成功的不敬。而郑成功对施琅则是一再忍让,终因施氏兄弟愈发张狂,不得不下令捉拿。杨英乃郑成功身边多年的书记官,一直随其左右,得其赏识,关系甚为亲密,在言及施、郑矛盾问题时,难免对郑成功有所回护,若以此论定施、郑交恶之责任全在施琅,显然有欠全面。
《台湾外纪》中江日升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但持令者乃德挚友,回而不述执法前言,徒诡说:‘尔欲以藩令胁吾,面叱杀之’之语。成功大怒。次日,传诸将入船,令右先锋黄廷收琅,并父大宣、弟显贵,交林习山守于巨舰,习山令副将吴芳看之。”此外,陈衍的《福建通志·施琅传》与此叙述基本一致,而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则更明确地写道:施琅“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从这些资料看来,曾德乃犯法当诛之逃兵,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而郑成功对曾德的眷顾则显然不当,为此而抒积怨,逮捕施琅及其父弟,则显然更加不当了。
//
………
嫌隙渐生施氏全家被囚(8)
………
以李光地的作品为代表的清史资料对此事也有记载。李光地在《施将军逸事》中叙述说:施琅加入郑军后,“郑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舱中,欲杀之。公以计脱,郑遂杀其父若弟。”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为施琅是清廷的有功之臣,故而对施琅有饰过之嫌,记载了郑成功逮捕施琅的事实,并把逮捕的原因简单地描写为郑成功嫉妒施琅,意欲加害之。显然有失公允,不足凭信。
各家史料所述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此时读书不多、缺乏涵养、好勇斗狠的施琅,斩杀曾德,成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则是可以确定的。曾德不过一介末将小卒,本无必要也不可能掀起如此大澜,令两位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反目成仇。真正导致两人关系彻底走向决裂的是施、郑之间长期矛盾的最终冲突,是两人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施琅自入郑军之后,尽展其军事才能,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其中以智取金、厦一役最为世人称道。施氏兄弟在郑军中分别统领着左先锋镇、援剿左镇两支劲旅,加之威望日隆,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有所忌讳。俗话说“功高震主”,施琅自幼自命不凡,咄咄逼人,多次拂逆郑成功之意,终被解除兵权,即使为郑军夺回厦门立下奇功,处境也难以逆转。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遭郑成功弃用令他怨气难消,深感前途暗淡,故多方滋生衅端,以发泄心中之不满与怨恨,“径自削发”、“辱黄廷”事件即是因此,曾德事件也是因此。
学界曾经议论曾德是否罪该致死,以及施琅是否有权处死曾德。其实曾德事件不过表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施琅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是对郑成功权威的公然藐视和挑衅。假如曾德的确罪不当诛,是否意味着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具有合理性?是否意味着非得施琅满门不赦?根据以后事态发展,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只是过程,而彻底剪除才是目的。事实上,以施琅高傲狂妄的禀性,无论曾德是否犯有死罪,施琅是否有权斩之,此时满怀愤懑的他都不会放过曾德,其性格注定要以此来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而同样满怀愤懑的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无论施琅斩杀曾德是否有理,结果大抵如此,也就注定了施琅悲剧的命运。更何况郑成功已派人传令勿杀,施琅却一意孤行,显然是对统帅权威的藐视,甚至有寻衅之嫌;加之郑成功派遣的传令者为曾德之“挚友”,此人大概太了解郑成功暴躁易怒的性格,因而不排除从中挑拨,以激怒郑成功的可能。天时地利竟然如此不巧,两位历史的骄子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裂了,进而引发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成就了各自的惊天伟业。试想,如果当时他们各自后退一步,历史会是怎样?当然他们的性格不会后退一步,就像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一定会成就大业一样的必然。历史真的很奇怪。
//
***************
*第四部分
***************
脱离险境后,施琅投奔郑芝豹,请其从中斡旋,以化解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然而等到的却是惊天噩耗。为报仇雪恨,施琅别无选择,毅然踏上西去之路——第二次降清,从此将姓名由“施郎”改为“施琅”。
………
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1)
………
此时,身陷囹圄的施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着亲人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施显早已被拘,父亲施大宣和所有留在厦门的亲属均被关押。施琅感到了颤栗,看来郑成功不仅要惩治自己,同时还迁怒于无辜的家人;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还要殃及至亲至爱的人。想到此,愤怒、羞愧伴随着不祥之感从心底升腾而起。
施琅既已被羁押,消息又从何而来呢?据《襄壮公传》记载:“时守公舟者,为林习山帐下,林故与公善,且敬事公,因嘱其善待。”负责关押看守施琅的忠定伯林习山向来对施琅十分敬重,因而与之关系十分友善。在接受了看守施琅的任务后,林习山心里十分矛盾,既为施琅的遭遇而不平,又难以违抗帅令,于是将看守施琅的责任交由副将吴芳负责,并嘱其善待之。郑军中有许多人都像林习山一样与施琅交好,对施家遭遇甚为同情,因而不顾危险,为其通风报信。因此,施琅虽身陷囹圄,但依然消息灵通。不久,有人捎来父亲施大宣口信:大限将至,父子同死无益,若有机会,你弟兄各自逃命去吧!施琅闻听此信,心如刀绞,然此时又一字条送至手中,内中只有短短一行字:“祸在今夜,速谋脱身!”字迹十分潦草,显然写就于匆忙之际。施琅不禁脸色微变,沉思片刻,随即大笑道:“此易与耳!”守卫士兵忙问其故,施琅曰:“藩欲吾输金二千,吾业有千余,再告贷数百则足矣。”众人信以为真,都为施琅即将解脱灾难而高兴。傍晚时分,施琅提出去借银子,卫兵不疑有他,一行二十余人遂押着施琅一同离船上岸筹银。行至一空旷偏僻处,施琅故意推说身乏,坐地不走,众军士疑心顿起,围了上来。冷不妨施琅霍然而起,迅敏地将士兵打倒在地,然后借着茫茫夜色,消失于茂密的树丛中。“夜二鼓,郑氏果遣人欲害公。见已遁,归报,乃环岛遍索。”前来杀施琅的人空手而回,郑成功立即下令全厦门戒严,遣人四处搜捕,并颁布命令:有藏匿施琅者,诛杀全家。
据《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逃脱后,为躲避郑成功的追击,藏身于山洞之中,昼伏夜出。连续五天五夜,施琅未曾觅得食物,饥渴难忍,自思长此以往亦非良策,遂决定冒险下山,去找自己的部下苏茂。天色微明时,远远望见一早起的农夫在田间劳作,施琅四顾无人,便上前问路。农夫乍见,十分惊愕,心想就算是急于出门赶远路之人,也不至于起得如此之早。稍近,农夫不由惊讶万分地叫道:“尔非施公乎?本藩悬赏格购公急,犹在此乎!”农夫将施琅带至家中,先向母亲禀明了此事,然后杀鸡煮粥,让施琅饱餐了一顿。施琅对他不顾身家性命的义举非常感激。在农夫家躲了几天后,搜捕施琅的行动没有半点松缓,施琅怕连累这良善人家,决定离开。乘着夜色,农夫带着施琅上路了,一直送出十余里地,方才洒泪相别:“公行矣!誓为公死勿敢泄。”施琅再三对农夫表达感激之情,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赶路,逃至时任左先锋镇的苏茂家中。
据《襄壮施公传》中所记,关于施琅逃难过程,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施琅告别农夫后,决定去找部将苏茂,夜雾中慌不择路,孤身来到大海边。不敢问路,只得藏匿于荒谷中,连续几天没吃东西,几乎饿死。这天一大早,施琅冒险出来寻找食物,正遇一退伍老兵在锄园种地,急忙躲入沟中。老兵远远地望见沟中卧着一只五花豹,惊得目瞪口呆,仿佛听见有人对其耳语:“是箕水豹避难到此。”待惊魂稍定,认出是施琅。施琅见只老兵一人,壮胆上前,向其问路并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老兵听说过施琅的才能,对他温言相慰,并给他拿来食物。施琅告知欲去寻苏茂,老兵又代为引路,将其领至苏茂处,方才离去。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但它折射出社会普遍存在的英雄情结,人们热衷英雄神话和被神话了的英雄。一方面人们对逃亡中的施琅寄予同情,另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英雄人物所特有的心理需要,更说明历史是后人撰写的这一事实。
苏茂曾是施琅部将,担任副先锋之职,为人磊落光明,重情重义。施琅突然出现,苏茂不禁悲喜交集,为安全起见,将施琅藏在自家卧房中,谋划营救之策。据《襄壮公传》记载,第二天,苏茂备好酒宴,召集施琅心腹旧将郑文星、张猷、杨文、林照及其弟林福等前来聚会。在酒酣兴浓时,苏茂故意试探众将,责备追捕施琅不力,众将尽皆面露愠怒之色,纷纷托辞离去。次日,苏茂再次宴请众将,又怒责众人,张猷、林照将筷子一掷,怒吼道:“若为公心腹,背义若此,吾曹何面目与俱生!”郑文星、杨文苏觉得蹊跷,追问缘故,苏茂见众将对施琅一片忠心,于是说:“君辈共仗义,是吾心也!”遂实告以“公今在是”。众将拜见施琅,相拥而泣。正在此时,一队人马奉命前来搜查苏茂的家。这些士兵逐个房间仔细搜查,最后搜查到卧房,只见苏茂之妻坐在床上,蚊帐高高地挂了起来,搜查者审视了一番,未见可疑之处。待搜查者远去,苏茂急入内室。此时,苏茂之妻已是两腿发软,站不起身,苏茂将妻子搀起,只见被子一掀,施琅从床上坐起身来。当天夜里,苏茂密备一只小船,领众将护送施琅上船。施琅终于平安离开了厦门,驾小船前往安平投奔郑芝豹去了。
//
………
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2)
………
施琅乘船离开厦门,族叔施福闻知消息,亲自驾船前来接应。施福于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旋即被题授为武毅伯原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