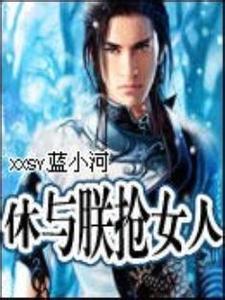女人如水-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泉儿反过来不相信了,“你是说,我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见报?”
“为什么不,写得非常好啊!”
犹豫了半天,泉儿说,“用是可以的,但要署‘泉儿’笔名,免得同学看到了笑话。”
方复明非常严肃地把脸一绷,道“叫什么‘泉儿’?太雅了,没有什么气势。‘始鸣’很好,从此开始,你郭始鸣,就要开始革命的鸣叫。”
郭始鸣
后来报纸出来,泉儿的文章以《女子教育之迫切》为题,发在“时评”栏中,文章的末尾,落有“始鸣”署名。将文章从头读至此,再看“始鸣”二字,确实有一种磅礴大气。也就从这一刻起,泉儿暗下决心,她要像秋瑾学习,像方复明学习,参与社会,改造社会,努力成为新一代知识女性。如崇德老人给自己取的名字,开始革命的鸣叫。
郭始鸣在《安徽通俗公报》上发表文章的事,本身也是新闻,很快在女子师范学堂沸沸扬扬传开。再与同学们相处,大家的目光中,都有一种敬佩。学堂监督吴传绮也得知了此事,在校园相遇,拦住她,问,“那文章当真是你写的?”
郭始鸣很有些不高兴地撅起嘴,“不是我写的难道是你写的不成?”当然,这话只压在心里,并没有说出来。
“好,写得不错。有思想,有见解,不愧是我们女子师范学堂的高材生。”吴传绮连声夸赞。又说,“《安徽通俗公报》办得不错,安庆街头,争相传看啊。”说至此,老人半眯着眼,沉浸于遐想之中,“我也一直想办份报纸啊,可惜时机不对。如果哪天办成了,郭始鸣,你可要来帮我啊!”说罢,呵呵笑着,一跛一跛而去。
郭始鸣不知道监督是笑话还是真话,但无论哪种,都足以让她心醉。
但很快,在最初的辉煌和兴奋之后,《安徽通俗公报》立刻转入平淡甚至十分艰难的维持阶段。
《安徽通俗公报》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省城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包括后来的谘议局议员王龙廷,皖北教育会的吴性元、杨元麟,等等。但这些资金,只能保证《安徽通俗公报》的启动,并不能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如果想要维持,最终还是要依靠《安徽通俗公报》本身的经营。但,方复明等热血青年,虽是革命宣传的高手,却不是经营的专家。报纸出版40后,老板张受泉开始收款,此时报社帐上还有资助款,收就收吧,并不显现什么窘迫。但随着时间推移,收入与支出开始出现严重背离,一方面,给各大书店代销的报纸款收不回来,而每天印报,都需要钱。另一方面,报社用稿,稿费还要继续往外开,特别是约过来的重点稿,稿费开得还不低。《安徽通俗公报》虽说有资助者,但人数不是很多,而资助的现金,也非常有限。到最后,多少有些坐吃山空的意味。报纸还要一天天地出,印刷费用也一天天增加,老板张受泉的一张脸,也一天天变得阴沉。逼得急了,报社同仁就以“革命大义”来压他。张受泉也很无奈,“即使我不赚你们的钱,但用纸要钱,用墨要钱,用工要钱,我也是小老板,实在是垫不起啊!”
那一阶段,方复明都在四处为经费奔跑,“只要把这个困难时机度过了,报纸才会转入正常的运转体制。”他说。
郭始鸣也想为报纸做一些实在的事,但涉及到经济,她的能力太弱,没有任何办法。
也就是在这时候,她想到了“方大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方大福
方大福
郭始鸣第一次把方复明与“方大福”联系起来,也只是十天半个月的事。
那天泉儿陪方复明走萧家桥去龙门口印刷局,在梓潼阁,正好与他三姐夫潘庆达相遇。潘庆达很热情,老远就堆着一脸笑,十分灿烂。但方复明沉着脸,要理不理。泉儿看不过去了,手臂捅捅他,说:“人家和你打招呼呢,也不回应一下?”见绕不过了,方复明这才勉勉强强尴尬一笑,向泉儿介绍,说是自己的三姐夫。
潘庆达说,“老父亲还是很想你的,有时间也回家看看吧。”
方复明支支吾吾答应了一声,拉过郭始鸣的手,就匆匆离开了。
方复明说他瞧不起他三姐夫,方复明少年时初出孔城镇,在省城开阔的革命视野,确实是潘庆达给指的方向。如果不是潘庆达带他去藏书楼听陈独秀的演讲,也许现在,他依旧是孔城镇一位大商家的阔少。但他赤着一双脚从孔城走到省城,报考安徽武备学堂时,潘庆达却已经调转方向,成为安庆新型的工商业主。潘庆达与普通的商人不同,他的眼光长远,插手的多是新兴的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如开办制作肥皂,洋油经销二级代理,这之中,也包括组建自来水厂等。方复明曾为这事与他进行过论理,但潘庆达振振有词,他说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他个人所做,而是另一条工业救国之路。其实方复明内心清楚,当年藏书楼演讲事发,参与者多遭到官府通缉,潘庆达也名列其中。后家人花重金进行疏通,又将他送到官府“自首”,这才得到宽恕,最后不了了之。经过这一挫折,潘庆达完全变了一个人,一门心思全部放在家业经营上。对外他由称是民族资本家,并把这块牌子,在安庆推得很响。
泉儿则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像他们家这样有钱,在安庆城,也能买半条街吧?”话语之间,淡淡的羡慕。
方复明不屑一顾,“他也算有钱?和我们家相比,也顶多只算个零头吧。”
郭始鸣抬头望向方复明,笑笑,道“哦,那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方复明望了望她的脚下,说,“你穿这双皮鞋,是从‘方大福’买的吧?”
“你怎么知道?”
“它是我们家在安庆城开的分号。”
看方复明一脸严肃,郭始鸣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方大福”是西城外一家鞋庄。换句话说,是前店后坊的皮革作坊。安庆的皮革业,多集中在荷仙桥至南庄岭一带。其中相对有名的字号“姚益兴”,咸丰年间创设,老板姚承德,既懂得制作,又懂得经营。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到宣统年间,已经发展为雇有帮工十余人的大店,生意十分红火,在安庆首屈一指。周边皮革作坊另有“董万兴”、“贾彰水”、“徐来明”、“刘少华”等多家,形成一定规模,这也是北城外一大特色。
但都无法与“方大福”相比。
安庆“方大福”是时尚的代名词。在安庆,无论是富家小姐,还是官员太太,只要,都会想到“方大福”。
“方大福”从孔城到安庆,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方复明。
方复明赤着一双脚离开孔城后,方大福又气又恼,后来自己妥协,想与儿子建立新型的互动关系。但方复明不屑一顾。在方复明看来,他们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方大福花巨资在安庆西城外盘下一处店面,把“方大福”招牌挂了出来,他的目的既明确又简单,不为赚钱,只为经常能与儿子见面。
但方大福毕竟是方大福,他只是在街上转了一圈,甚至到天足会去看了看,就为安庆城的“方大福”定下了经营方向。专攻时尚的男鞋与女鞋。他带了两个学员,带着他最喜爱的九姨太,坐船到上海,把南京路上的鞋庄一一看了遍,只要九姨太喜欢的样式,他都十分大方地为她买了回来。事实上证明他是有眼光的,或者说九姨太是有眼光的。女人脚上的裹脚布被撕碎后,各式各样的女式皮鞋便在中国有了“婆家”。而这种趋势,如一阵风,从上海滩刮出来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包括长江北岸的城市的安庆。
安庆城内“方大福”定下经营风格之初,城北的“姚益兴”,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甚至还有一些鄙夷。在他们看来,虽然天足运动初起波澜,但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女人天生就是小脚,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而这种状况,决定“方大福”不会有什么好的市场。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方大福”一开张,就引起了新潮女性的注意,官太太,富家小姐,女学生,等等,烟花女子更是争相光顾。半年下来,不仅生意如火如荼,而且基本抢占了安庆城以及周边六邑的女鞋市场。
郭始鸣也是其中的常客。
老爷子
郭始鸣是出八卦门走向“方大福”的。来的路上,她做过好多场景设置,带一种什么样的气势进店,进店指名点名找谁,找到之后话怎么说,遇到拒绝如何争取,什么时候动之以情,什么时候晓之以理,等等,考虑得非常仔细。但她没有料到的,当她迟迟疑疑走进店铺后,坐在柜台之后的一位的老者,手持烟袋,脸上浮着难以察觉的笑意,迎面向她走来。他的神态安详,他的气质轩昂,他的眉目慈善,他的笑意温和,当他立在郭始鸣面前,与她四目相对时,郭始鸣心中,没来由一种紧张。也许,气势压人吧。
“你终于来了。”他说。
郭始鸣不解地望着他。“你认错人了吧?”
“我方大福一辈子没认错过人。”
郭始鸣知道先败了一着。一个肯为儿子把家业从孔城迁至安庆来的人,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到?郭始鸣垂下眼,看他手上捧着的那根烟袋。真是一根好烟袋,七寸十三节,黄如金,缀有一根拇指大小的翠玉,绿到晃眼的地步,郭始鸣看它的时候,颈部略略发热,似乎与自己的那块玉佩是同一块料上切割下来的,而此时,两块玉心有灵犀,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交流。
“我知道你是背着方复明过来的。有什么事,你说。”
“我,只是随便看看。”
“依你的神情,绝不是。”
郭始鸣想了想,鼓起勇气,抬高了声音说:“你知道你儿子现在过的什么生活吗?他和他的同仁,几乎天天都为吃一餐饱饭而发愁。为了办好《安徽通俗公报》,他厚着一张脸,四处求助,也不顾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低声下气,连我都看不过去。他是为了他自己吗?不是,他是为了他的革命事业,为了同胞的幸福。你是他的父亲,还口口声声还说爱他的呢,为什么不给他一些支持?”
沉吟了半天,方大福道:“不是我们不给,而是他不要啊。”又说,“真的对他不理解啊,有这样好的条件,完全可以安安逸逸过他的富裕生活,为什么还四处奔波,搞什么革命呢?”话说至此,老人眼中,闪烁出泪水。
郭始鸣突然心动,她有些可怜这位长者。年近九十,活着的全部内容,就是他心中的明灯——方复明。但些时的方复明,却让他担惊受怕。“我一个女孩子,不懂你们大男人的心胸,但我知道,你们都有各处的追求。你一生以经营为平台,以赢利为目的。而你儿子,他的目的,是唤起民众,推翻清王朝。虽然道路不同,但两者都是目的,你为什么要强求于他?”
老人没有多说什么,他回过头,朝柜台那边使了个眼色,帐房先生立刻拿着两张银票走过来。“这是两千两银票,你先拿给他,如果不够,你再回来。我已是垂暮,没有后代,守着这些财产又有什么用?”
临出门时,老人喊住她,又补了一句。“如果他说你什么,你千万别反驳,只要他能把钱收下,”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