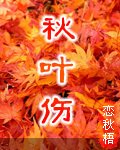半轮秋-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屠生又说:“咱们家乡的肥猪,不是‘洋种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哼,龟儿子现在的一些‘洋鸡、洋蛋’,中看不中吃,农民都不吃它。咱们家乡的猪,才是正宗祖传货。杀开一看,‘巴掌膘’,但肥得不腻人;瘦肉也瘦得细嫩……”
人家说:“晓得,晓得!”
屠生更来情绪了:“咱们家乡的肥猪,农民抽不来胆红素,‘肝胆脾胃’俱全!不像现在一些龟儿子城市周围的人,啥都兴起来了——抽了猪的‘胆水’,就往肉里注清水。那肉‘水垮垮’的,啷个吃嘛!”
人家着急了,说:“龟儿子屠生,你把你家乡的猪肉说得‘赛天仙’,那也不带两刀来我们吃吃,光耍嘴皮子。”
“嗨——就是叫你们拉呢!”
“不要钱?”
“一两刀不要钱,多了咋个不要钱呢?”
“多了啥价钱?”
“整毛猪,两块钱一斤;整车地拉,还要优惠。”
“那一斤毛猪杀多少肉?”
“7两肉,1两5钱骨头,1两肚腹……”屠生“一口清”。
“那你能联系得到不?”
“要多少,给多少!”
几个老同学认真了,冷静地合计后,当场敲定下来,到个体户那里租一辆“黄河牌”大卡车,第二天就开到咱们家乡去。
屠生坐在驾驶室里带路,一路上自豪得很,活像当年他的父亲给穷苦山区带来了红军队伍。车才到村口,他就喊司机将车停在机耕道上,又对着院子惊抓抓地喊媳妇:“快把那3头大肥猪吆出来!”猪吆到后,南充来的人就用随车带来的磅秤一过,当场就“哗哗哗”地给他数起了票子。这时,周围已经围上来许多群众,屠生把钱拿到手后,往头顶上一扬说:“要交肥猪的,快送来,1块8角钱一斤,车装满了就不收啦!”
半个时辰后,一卡车肥猪收满了。还有的村民吆来后,车已装不下,就直骂屠生咋个不多带几台车来,屠生就笑扯扯地说:“明天他们还要来哩。”
屠生这一仗打得很漂亮,简直像《西厢记》里的白马将军,带人马到普救寺解了崔莺莺一家的围一样来神。一连10多天,屠生都满面春风地带着他南充来的老同学,挨村挨户地收购肥猪。
奇怪的是,农民们得到了利益后,并不怎么感谢屠生。他们最关心的是屠生这回赚了多少钱。但谁问屠生,他都不讲。村民们也知道,你龟儿子屠生,也只养了3头肥猪,为啥包包就鼓得比我们高?还不是赚了我们的钱!心里就不大舒服他,可又说不出什么名堂来。村民们还非常关心他南充的几个老同学又赚了多少钱。人们问他时,他还是不讲。我反复问过他后,他才鬼头鬼脑地说:“差不多对半赚吧!”
屠生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留他吃过午饭后,他便离去。母亲来收拾碗筷,她脸上就有不愉快的神色。我说:“妈,屠生才是聪明人啰,事情办得漂亮哩!”
母亲说:“聪明啥嘛,还不是游手好闲的后生,地里的活路一点也不想干。”
我说:“他做信息员,占用了时间地里的活干得少些,也不能怪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探子屠生(4)
“啥信息员啰,是探子!还不是想赚点钱。”
“探子赚了钱,也帮了你们的忙呀。这就是市场经济。”
“我不懂啥是市场经济。我晓得他是吃不下地里那份苦,才去当探子的;是当了探子后,才赚了钱的!”
我忙说:“妈,你种庄稼、喂猪、养蚕赚钱,与他当探子赚钱,其实都是一回事。就如你家的‘洋马儿’(自行车),你是后轮子,用劲大,他是前轮子,管方向,离开了哪个轮子都不行。”
“那才不一样呢!我们家赚的那些钱,是正路。他游手好闲赚了钱,都不光荣。”
“你家去年养蚕子,桑叶不够喂,蚕子都快饿死完啦,那就光荣啦?”
母亲一听这话,立时打了一个“哈哈”。随后就来套我的话:“那屠探子把这些事都告诉你啦!”
我说:“这有啥不能说嘛。”
我也就顺便核实起屠生上午介绍这件事情的真伪来。
屠生是这样谈起的:“你家的蚕子养得好啊!每年都是两三张纸。”
我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以农桑为本。听说,我奶奶那一辈,就是蚕养得好。昨天我去看了一下自留地,地里还种仔桑200株。真不简单!”
“搁倒起!去年你家养的蚕,要不是我帮忙,不饿死光了才怪!”
我一听还有这事,就非让他讲讲不可。他又点了一支“红塔山”,吧嗒吧嗒抽了几口后说:“都怪你妈胸口子厚,碗头还没吃完,就在想锅头!”
他说,我们家200株仔桑,按说养3张蚕纸就合适了。但母亲坚持要养4张纸。说去年养了3张纸,桑叶都够用。桑树一年长一截,浪费了桑叶可惜。于是,她就带头买回了4张纸。其他村民受她的影响,也都多买了半张纸。
这屠生是精明人,春蚕才二眠起来,正是插秧打谷的大忙时节,他农活让媳妇干,自己扛一杆猎枪,全乡满山满岭地跑。头天傍晚回来,他的枪尖上挂一只野鸡。人家不问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一炮‘横火’打中的,你看还是一只公鸡呢,多肥!”第二天傍晚,他的枪尖上又挂一只兔子,逢人又会自言自语地说:“一炮‘跟火’打栽了的。狗日的,三瓣嘴,撞到枪口上了。”
村民们大都不理会他,知道他是“探子世家”,舞枪弄炮,自有祖传。谁知没过几天后,村民们就着急了,桑叶不够用,春蚕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蚕子缺桑叶,简直比熊猫缺箭竹还难办,几乎没有任何饲料可以代替。三眠过后的蚕子,食量又大,桑叶一缺,不是饿出病来,就是做不出茧子,等于白养。如果一个村的一家一户缺桑叶还好办些,互相拼凑一下也就过去了。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叶子,谁拼凑给你!这等于像20世纪60年代初那样大面积地闹饥荒,你去找谁“讨饭”。眼下,在这群“饥民”之中,饥荒闹得最凶的,当数军属邓老太婆一家了,她家养了4张纸!
母亲是急性子人,又是爱面子的人。一看自己的谋划失败了,春蚕已经开始互相噬咬,就急得抓耳挠腮,像千万只蚂蚁在啃她的骨头,终于一病栽倒在床上。
屠生这时来了。他嘴里叼支烟,走到母亲床前,笑扯扯地说:“邓老太婆,蚕子缺叶子吗?你家不缺票子嘛!赶场天到街上摆个摊子,比起票子,收购叶子就是了嘛!”
“你打的好烂牌!”母亲气得骂他快出去。因为养蚕人谁都知道,桑叶这东西,缺了是“金叶子”,剩下了不如“树叶子”。既吃不得,又用不得,但你若是一旦上街收购桑叶,别人就知道你要的是“救命叶子”,不但要随意抬高价钱,而且有时还不给你送来。大家都懂得,这桑叶送来少了,卖不到几个钱;送来多了,你又“吃”不下,放不住,哪个天天给你背叶子来呢?因此,桑叶从来形不成市场。
“邓老太婆,侄儿自有办法解你老人家的难。”屠生这时才一脸正经地说,“那几天我满山满岭去打猎,哪是去图吃那几口野味,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你家和全村养蚕人找‘闲叶子’呢!”
“找到了?”母亲一下来了精神。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你老人家再养4张纸也‘吃’不完!”
原来,屠生看到一个村的人今年普遍都增养了蚕纸,知道桑叶要闹饥荒,就扛上猎枪,云游四方,与那些养不起蚕的人家做了商量:“你这几排闲桑树,巴掌大的桑叶闲着多可惜。还挡了光线,误了庄稼。到时候,我找养蚕人家来把你们的叶子‘包’了。按树头计钱,茧子上市后我再来算累账。”随后,定下了每树桑叶的价钱。现在,探子的情报用上了。
屠生讲完这些情况后,就带着我妹妹和其他缺叶子的村民,背起背篼,沿他打猎的路线往山里走。几里路处,他放下一拨人,叫他们去找谁谁谁家联系摘桑叶;几里路处,又放下一拨人,叫他们去找谁谁谁家收叶子。
钱,他不准直接付给卖主,只准给人家每次打张摘走多少斤叶子的欠条。茧子上市后,他才拿着这些欠条,挨门挨户到收过叶子的人家收钱,价格倒很公道。
探子屠生的这一招,尽管又一次帮了乡亲们的大忙,但事后乡亲们一想:你龟儿子屠生,只凭扛杆猎枪,悠悠闲闲地转几天山路,就比我们担惊受怕养一季春蚕的收入还多,心里又不平衡起来。母亲,大概就属这类人中的一员。
我与母亲核对完事实,母亲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说:“妈,人家跑了路,一斤桑叶才多收你5分钱,人要讲天地良心,不该歧视他。”
母亲便说:“倒也是这个理,但就是看不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我说:“这不叫游手好闲,是他当探子的一种工作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很重要,就是要有一批人,去当信息员,偏僻山区的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母亲近年来已不太爱听这套官话了,但这回似乎听入了耳。她边收拾杯盘碗筷,边用玩笑的口吻说:“你在外面走南闯北,那咋不也去当当探子呢?”随后愉快地离去。
第二天早饭后,屠生提了两布袋“七星椒”来,叫我带上:一袋自己吃,另一袋送给成都几家有名的火锅店。说如果他们感到味道好,就写信来,要多少,运来多少,但价格要公道。可惜我未能带上这些东西,因为一早,我就起程归队了。他的这一任务,我终未完成。
买票(1)
居住大都市,空陆码头齐全,自己出门方便,却也带来一层麻烦:替人买票。
如果来客是公干,离埠时间、路线、票种并不苛求,买票的难度自会小些;如果来的是头回进城的农民兄弟,要买的又是春运高峰期去广州、深圳、北京等热闹地方的火车客票,事情就复杂了。
我家乡在省城谋事的不多。近年兴起的农民进城打工热,远比当年城市知青下乡热还要壮观火暴得多。他们过完春节后,就要急匆匆去遥远的地方打工。离乡时,大约已经瞄准你这个城里“目标”,满怀信心投奔你来了。
家乡人是很重情义的,进城托人办事,绝不会空脚耷手而来,总要带上一些土特产品。临走那天早上,他们从鸡圈里按上一只大红公鸡,捆住双脚,装入旧麻袋或编织袋里就搭汽车赶来。我家住在一个军事管理区,进院子大门就有许多周折,越往里走难度越大。好客易问到家门了,可主人并不在,他们就会张头探脑地在门前等候归来。这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大红公鸡千万别在口袋里憋断了气。新春节气的,送一只死鸡不吉利,赶紧从袋里取出放风。一个来小时后,你门前就有了一堆鸡屎。那时你与家人也该回家了,一见这景象,再听这口音,便知是家乡来人。至于叫什么名字,你不一定叫得出来,也不必去细问。就赶快从他们父母的脸相上去寻找各自是谁家后生。
“高如爸,我是陈狗娃的老大呀!”这里叫你“爸”,并没有血缘关系,就像《阿Q正传》里未庄人叫某人什么“爷”一样,完全是一种恭敬。
“都长这么大了,快进屋来坐呀!”
或是几家兄弟,或是几对夫妇,准保将你客厅的沙发坐满。
“怎么身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