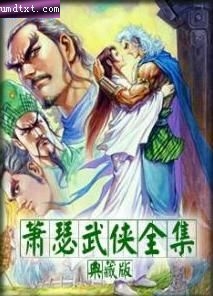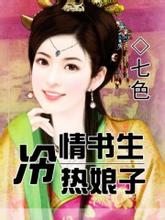太学书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是辽水的上游——据契丹人自己的传说,骑白马沿土河而来的男子与驾青牛沿潢河而来的女子在木叶山相遇,结为配偶后生八子,而后繁衍成八部,这就是契丹一族的由来。
“迟至唐朝,契丹已经是北方的大族。契丹人相传,唐朝初年皇帝曾赐姓契丹族长为李氏,并加封为松漠都督。但在唐则天女皇当政时,契丹不堪汉人都督的凌辱,与唐发生了连年大战,终为唐所败,不得不向北依附于突厥,并时常受邻部奚族的侵扰。那时北方各族在大唐的压迫和挑拨之下,常年不得安生,哪一族强大后都会遭到大唐联合其他各族的打击,这个局面直到安史之乱开始后才得以改变。那些年里,中原一片大乱,而契丹人则说他们族中最伟大的英雄阿保机就出生在那个时期,并带领他们真正走向强大。在朱全忠逼迫唐昭宣帝禅位的那一年,阿保机也在北方作了皇帝,从此契丹人开始独霸北方,进出中原,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了。”
“以后石晋塘卖国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讲座下的一个青年毫不客气地打断赵良嗣的话,然后问道,“这帮胡虏霸了我燕云十六州这许多年,以仁宗皇帝夹开国之兵也不能取胜,我倒想知道他们到底强在哪儿?”
赵良嗣毫不生气,还对发言的青年挑起大拇指赞道:“问得好!这位小哥肯这样想,足以证明我中原也不缺强人。老夫记得,有一位当朝显贵告诉老夫,太祖皇帝当年密谋,曾想以二十帛购一契丹精兵人头为价,准备以两千万帛购得契丹十万精兵的人头,为此建立了三十六个国家仓库。太祖皇帝的估计没错,契丹全盛之时,其精兵也不过十余万人,他们百多年来就一直以这十万能战之士压制了燕山以南的整个地域。”
讲座下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赵良嗣也不惊慌,静静地等待这片声音消失。终于,书生们的感慨声停止了,又有一人站起来问道:“敢问先生。”——他们首次对赵良嗣使用敬语——“契丹能够以小制大,以少制多,到底是因为什么?他们的内部情景到底是怎样的?”
“契丹人比汉人少几十倍,国土却不比汉人小,他们自然早有制度应对,”赵良嗣也从容应对道,“契丹本以游牧渔猎为生,自占得燕云十六州以来,并没有把汉人迁走杀绝,以本族人填之。他们知道,要填也没法填得满。所以,契丹人实行了南院、北院制度,对契丹和汉人分而治之。汉人耕田、贩货、交纳赋税;契丹人则游牧、渔猎、征战掳掠,大辽皇帝虽屡屡强调南院、北院同等重要,可是谁不知道,北院契丹人的系统才是大辽国的根本所在。大辽皇帝为了保持本族的征战优势,也是煞费苦心,几百年来,总结出了四时捺钵制和寒鲁朵宫帐制——契丹语中称皇帝的宫帐为寒鲁朵——这寒鲁朵宫帐制的核心其实就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制,只不过内容比侍卫亲军包含得更多更彻底一些。
“每一位大辽皇帝登基都会在亲近自己的各部落中遴选几万精兵做为自己的寒鲁朵,一旦被选中,这些精兵连同他们的亲属就都成为了皇帝的直属部下,从此后,不管皇帝在哪里,他们都要随侍左右。打仗时是辽军中的核心部队,平时也要为皇帝采办物资、造作器具,等到皇帝驾崩,他们还要全体去为皇帝守陵,而新皇帝又会再次遴选自己的寒鲁朵。”
讲座下的议论声仍然不绝于耳,有人讥笑道:“夷狄就是夷狄,岂懂圣人治国之法。”有人不解道:“强夺民间劳力如何抽税?不抽赋税何以养官?不养官吏何以治民?”这次赵良嗣没有理会这些声音,他继续说道:“契丹人绝大部分聚部落而居,部落贵族往往也是国家重臣,部落贵族一般可以自行决断本部落内的一切事物,皇帝也很少干涉,但是他们也有战时为皇帝出兵的义务。自进入中原以来,契丹人的财富增长很快,还仿效中原建立了五京之制,但是他们的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并不能和大宋的四京相比,不过是夸强自傲而已,并不曾因为有了五京而改变自己多少。而且契丹人也很适应和喜爱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随水草,逐寒暑,奔走在天地间,也自以为欣乐,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免俗。契丹语称皇帝的临时行帐为‘捺钵’,犹如大宋所称的‘行在’,而大辽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大辽境内几处最好的地方。
“一般而言,大辽皇帝的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泊捕鹅或在混同江钓鱼,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避暑、张鹰,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射鹿,冬捺钵则在永州广平淀猎虎。皇帝去捺钵时,大辽的大小官员、内外臣属都要随行,而夏冬捺钵时常常会由大辽皇帝主持北南大臣会议国事,那就更是大辽决断大事的时候,所以契丹自有其法度,决不可与中原等同视之。”
赵良嗣停下了他的介绍,看到讲座下一片惊骇、茫然的神情,这是他不止一次在大宋臣民听完他的话后看到的表情。他知道,他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封闭已久的窗户,让他们模糊地看到了一片难以置信的景象。有的人会断然回头,怒斥他赵良嗣是骗子,绝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的事;有的人则毫不在意,以为这是大相国寺新出的说书段子;还有的人则茫然若失,不知道他赵良嗣说的为什么跟前辈先生说得不一样。不过总有一两个人会仔细想想他的话的,他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赵良嗣拱手下了讲座。他并不打算和那些太学书生就大辽的问题辩论下去,他已经在这里盘恒半日了,而且根据他的经验,一旦他陷入到这种辩论中去,他今天甚至于连续几天都不要想做别的事了,而有一件事是他今天必须去做的。所以,赵良嗣礼貌地摆脱了一些提问的生员,只是由陈东陪同着走向室外。
陈东此时也在极力挽留赵良嗣,他略显激动地说:“先生讲得太好了,当真有推窗望月,如沐新风之感。”
赵良嗣客气道:“哪里,哪里,实在是过誉了。”
陈东又说:“先生今日所言具只在于介绍大辽内部情景,而对如何应对大辽却不至一言,不知为何呀?”
“嗬,嗬,”赵良嗣有些尴尬的笑了,“如何应对,你们太学诸生应该自有良策,岂容老夫班门弄斧。”
陈东直视赵良嗣,真诚地说:“我辈学生难免有种种狷狂自傲令人不屑的表现,可是他们都是忧心国事的热血男儿,从不以为国事当头应该置身事外。”
赵良嗣说不出话来了,他知道陈东把他当成那种因循苟且从不以诚待人说心里话的老头了,可是他正在做的机密大事也确确实实是不能随便和人说的呀!面对陈东的双眼,片刻权衡后,赵良嗣拉着陈东的手臂,把他引到了一处僻静的墙根下,郑重地说道:“从昨天到今天,公子的为人老夫处处看在眼里,早有一见如故的亲近感受。实不相瞒,今日老夫已经为公子耽搁半日了,老夫实在是有一件大事要做,做成之日,你们太学诸生也会喜不自禁。”
“可是为了对付大辽?”陈东敏锐地问道,同时两眼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赵良嗣被陈东一语说中,心中暗暗有些后悔,他不置可否地说:“近日老夫就要出一趟远门,确实没有时间陪伴公子了,不过我答应公子,只要老夫一回来,就陪公子谈上三天三夜,如何?”
陈东哪里肯放他走。他反抓住赵良嗣的手臂,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声音说道:“先生不能就这么走啊!如果先生是去大辽?小可斗胆请先生一定把我带上,只要能去大辽,让我干什么都行,书童、马夫、挑夫,我什么都能干!”
赵良嗣被陈东的话吓住了,他着急地说道:“公子嚷不得,嚷不得。此乃机密大事,朝中重臣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啊!”
“好,好,我不嚷,”陈东说,“只要先生让我去我就不嚷。先生放心,陈东不是无用之人,骑马、登山、埋锅、造饭一切野营事务我都懂得,不瞒先生,这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我还是走过几回。”
赵良嗣眼看陈东情绪如此激动,同时被他的真情所感动,心中陡然也生起了一股豪气,他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做,可他还是说道:“公子既有这番胆识,那就请公子掌灯时分来寒舍一聚,到时公子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陈东仍然不想放开赵良嗣的手,他不放心地说:“先生不会骗我?”
赵良嗣笑道:“公子放心。”
赵良嗣终于摆脱了陈东抓住他的手,他整整衣冠,与陈东拱手告别后即沿太学门前的大街而去。走出几步后,这个一脸长须的风霜汉子竟回过头来用略带调皮的神情说道:“也许你该和你的家人告别了,顺便剃掉你的长须,换下你的长袍。”
陈东一愣,随即明白了赵良嗣的意思,那是要他改变儒生的面貌啊!也是肯定会带他走的切实保证。他轻拂了一下胸前的三缕长须,“哈哈”一笑,转身即向街上的剃头铺走去。
同样是跨越汴河,在州桥东边,相国寺桥的北端,繁华的东大街后,一条不引人注意的小巷静静地把喧嚣隔绝在了几丈以外。由于靠近汴河,这里路面的青石板缝间挤满了苔藓,配合小巷两侧人家园中伸出的青青竹枝,任何人走到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安详、闲逸起来。
陈东拍响了这条小巷尽头一个小院的门扉。过了好久,一个十岁左右丫鬟装束的小女孩才来打开门,她一看是陈东就笑着说:“呦!陈公子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昨晚还不够尽兴吗?我家小姐尚未洗漱,请公子晚上再来吧。”
陈东一把推开门,边向里走边说:“等不得了,琴儿,我有要事要和你家小姐讲,你快去伺候她洗漱吧。”
说话间,陈东已进了厅堂,他随意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就又催促那个小丫环。小丫环吃吃笑着进了里屋去了。
过了片刻,小丫环搀着一个略施粉黛的年轻美人飘然而出,小小的厅堂也因为这位丽人的出现而瞬间明亮了许多,只见她对着陈东微微一笑,然后就以令人愉快的声音喝斥她的丫环:“琴儿,怎么不给陈公子上茶?这么没规矩!”
被称作琴儿的丫环反驳道:“只要能早一刻接小姐出来,陈公子就是没茶喝也乐意的。”
“贫嘴,”年轻的美人还是用她那让人无法害怕的喝斥说道,“还不快去沏茶。瞧我一会儿怎么罚你。”
琴儿转身走了,厅堂上剩下的两个人一时谁也没有说话。陈东伸手想要拉年轻美人的手,美人一甩衣袖躲开了,背对着陈东悠悠说道:“一大早的你不就说有要事要办非走不可吗?怎么这会儿只是剃去了胡子、换了长袍就又回来了吗?”
陈东满脸歉意地说:“霏霏,真对不起,我一直说要好好陪你的,可是今早因为要请一位奇人给太学中的生员讲课,所以要早早离开,我本来想过两天再来好好给你赔罪,但我现在可能要出远门了,所以我一定要来和你告个别。”
被称作霏霏的美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说道:“我本来不过就是个青楼女子,你要来就来,想走就走,何必跟我编这些鬼话。”
陈东见霏霏并不相信他,急得站起身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