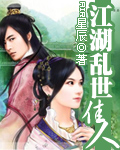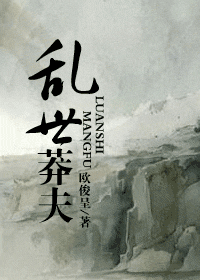乱世浮生-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29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不久,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一度代理过中文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刘文典未能及时随学校转移到后方,整日闭门不出。1938年下半年,他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1943年,因故被解聘,转而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解放后,刘文典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先后开设“温李诗”、“杜诗研究”等课程,还主持杜甫研究室,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肺癌在昆明病逝,终年67岁。
“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1)
战争剧烈地改变着社会,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战争而处于失衡的状态。当然,战争也会改变处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轨迹。应该说,抗战之前的丰子恺并不追踪社会的热点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革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战前的丰子恺于社会是隔膜的,他全身心地融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吟诗、作画、饮酒……在童真和自然的天地里他充分感受着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乐趣。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之前的丰子恺是有几分出世的,丰子恺故居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都市隐者。但战争却改变了这一切。在抗战爆发之后,丰子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什么转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的目光停留在哪里?何处是他的牵挂?
抗战爆发以后,过去集中在都市的艺术家、作家开始奔向抗战的后方。尤其是在上海战役爆发之后,文化人纷纷南下。但是,此时的丰子恺却并没有加入这支南下的文化大军,而是举家由杭州搬迁至他的故乡石门湾。对于一个在战前几乎是不问世事的艺术家,在此时有如此行为当然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对于自己的行为,丰子恺后来解释其中的缘由说:“第一缘缘堂(丰子恺故乡寓所名)是安息之所,归宿之处,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难以割舍。与其死在野外,不如与他同归于尽,一时大家舍不得抛弃这些累赘之物。第二,石门湾本地人就误认这里是桃源。谈论时局,大家都说这地方远离铁路、公路,不会遭兵火。况且镇小得很,全无设防,空袭也决不会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战争伊始,丰子恺并不想因战争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实际的抗战活动。或许此时丰子恺只是准备做战争中的隐民,在战火纷飞中继续营造自己温馨的世外桃源。尽管汉口和四川的朋友不断写信给丰子恺,让他早日离开处于战火中的故乡,但此时的丰子恺却还沉迷在温馨田园生活的幻梦中,他不愿意离开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不愿意离开他亲手建造的带给他无限快乐的家园。1937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丰子恺的40岁生日,这时相距不远的松江已经失守,嘉兴也已经是炮火横飞,但处于乡村的石门湾表面却平静如初。此时的丰子恺显然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尽管他知道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但他却总觉得这场战争相隔自己很遥远。因此,即便在此时,丰家还是在为丰子恺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寿筵,充满了一派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作为一个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具有出世思想,追求无拘无束、自然适意的日常生活境界的艺术家,抗战始发,沉迷在自我营造的幻影中,有此种行为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毕竟他还没有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来临。丰子恺后来也反思过自己当时的行为,他说:“上海南市已成火海了,我们躲在石门湾里自得其乐。今日思之,太不识时务。”幻梦毕竟只是幻梦,丰子恺最终还是会觉醒,正如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中所说:“在前线流血的,在后方流汗的,在没落的涡流中挣扎的,在敌人的裤裆下扮鬼脸的,映照之下,嘴脸分明:有血型的这边来,缺人性的那边去。——中间隔着一条抗战的鸿沟。”在无情的战火中,哪里都不会有温馨的桃源。
1937年11月16日,跟往常一样,丰子恺继续着自己平静的家居生活。这一天丰子恺正在缘缘堂阅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准备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无数事件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编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可就在这一天下午,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江南小镇,也成了日寇屠杀的战场。日机对石门湾狂轰滥炸,当场炸死三十多人,伤无数,其中有一颗炸弹是对准缘缘堂而投下的,万幸的是,丰子恺的家人都只是受了惊吓,皆平安无事。丰子恺回忆说:“我们的房子最高大,最瞩目,犹如鹤立鸡群,刽子手意欲毁坏他。可惜手段欠高明。”严酷的现实使丰子恺彻底清醒了,他终于明白,在无情的战火下,缘缘堂并不是温馨的桃源,他的桃源幻梦彻底破灭了。在现实的刺激面前,丰子恺决定不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尽管舍亲别友,举家逃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丰子恺依然决定“我决定到长沙!否则半路转入沟壑!但绝不愿居浙江!仙居也许比长沙好,但我决定要到长沙”!眼见的人间惨剧使丰子恺回到人间,尽管他喜欢温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但是当国恨和家仇一痛,怒火和炮火齐烧之时,他便不再孜孜于充满趣味的自我生活天地,而是把个人解脱和一切众生解脱相统一,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2)
11月21日,丰子恺一家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亲友们匆匆话别,登上一只小船告别了石门湾,踏上了逃难的路途。此时的丰子恺心情颇不平静。作为一个佛教徒,丰子恺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认为:“真是信佛,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该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对于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丰子恺饱含着对他们的同情,“我每次设身处地的想像炮火迫近时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佛家历来强调慈悲为本,作为佛教徒,这种慈悲心也自然渗入丰子恺的精神血液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民众逃难由此心出发,丰子恺不能不对残暴的侵略战争表示极大的愤恨,同时他还以己度人,希望能将一切众生带到一个太平的地方,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惨剧,没有残暴的所在。在离别石门湾时,看着众多亲友乡亲脸上悲戚、惶恐的神情,丰子恺极其沉痛,他哀伤地说:“这使我伤心!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丰子恺离别故乡时的悲哀和伤感,同时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炮火硝烟中佛的慈悲和梵音的空远。
“还我缘缘堂”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进而今虽报空军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是丰子恺在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中有他离别故乡的伤感,有乱世飘零的忧伤,有对战火毁灭美好的感叹,有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词的后两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文章风格,明显与在此之前雍容有度的文风形成极大的差异,这种文风的差异表明,抗战之后丰子恺开始了由隐士到斗士的路,尤其在获悉他的精神家园“缘缘堂”被毁之后。
自1937年11月始,丰子恺携全家老幼开始逃难,一路饱经流离之苦。于逃难途中,1938年2月9日,丰子恺接到朋友从上海发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面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得此噩耗,丰子恺默默无言,他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缘缘堂在炮火中蓦地参天,蓦地成空的景象。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他苦心经营的人间乐园毁于一旦时,他的思想怎么能不发生转变?丰子恺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而有出世的思想,因而对世间的一切都取冷观态度和趣味主义,他能够看穿一切,坦然自若;但另一方面,丰子恺又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和感情丰富的人,他不可能真正做到对世事的冷眼旁观,摒弃对群体的关怀,他不能不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家园的被毁促使丰子恺面向广阔的现实,从缘缘堂的灰烬中走出来的是一个金刚怒目式的丰子恺。他写道:“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此后,他用充满激情的笔相继写下了《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文章,文风为之一变,文章痛快淋漓地指斥侵略者,自豪地歌颂民族精神,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文章中他写道:“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欢喜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知我比炸弹力强得多。目前虽有炸弹猖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
缘缘堂的被毁对丰子恺似乎是一个界标,他的人生态度开始由佛家的消极转向儒家的积极,他的大量散文和漫画都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爱国者的责任,自此开始,丰子恺便告别了自己冷眼旁观的隐士生活而回到人间,他的文章和图画也开始具有人间烟火,凛凛然是条汉子。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成为《抗战文艺》编委之一,并且为《抗战文艺》的创刊号画了封面、题了签。在武汉,丰子恺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他置身于抗日的洪流中,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尽情发挥着他各方面的才能。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评论此时的丰子恺说:“他本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战后呢,由我看来,却是很积极的了。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他勇敢,坚决,乐观,和一切的战斗者一样。作为证据的,是他一年来的行动和言论。用画面强烈地控诉了战争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罪恶。用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揭露日寇暴行,以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另一类作品中,则表现了人民热爱和平,企盼战争尽快结束的愿望。”
由于此时丰子恺积极宣传抗战,需常在外奔走联络,为了行动方便,他脱掉了平日惯穿的长袍,改穿中山装,神态异常活跃。此时的丰子恺与往日大家对他的印象判若两人,著名作家王西彦描述此时的丰子恺说:“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超脱出世的样子。”友人们戏称丰子恺“返老还童”,并对他说:“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有意思的是,大约是这句话传开去了,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丰子恺割须抗战”的消息。消息传开,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是否确有其事。但事实上,丰子恺并没有剃掉他自1927年起蓄的长须